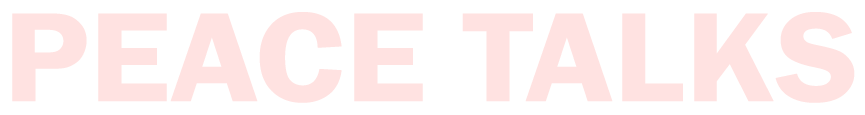告台灣同胞書(53):鸚鵡會說人話嗎?
告台灣同胞書(53):鸚鵡會說人話嗎?
陳真
2025.03.15.
我絲毫無意說自己看事精準,低能者才會有此心思,畢竟許多判斷只是一種ABC,哪需要什麼本事?哪需要什麼知識?當你長期幾十年來關注一件事,你不可能不懂得那些顯而易見的東西。
我之所以表明這一點,只是希望人們把我說的話當真。它當然不一定都對,但我一般不說沒把握之事,我也不喜歡做什麼分析推測,我覺得那很無聊,自說自話,瑣碎而缺乏意義。
關注大局才是重點,至於各種細節的陳述並不是為了細節本身,而是藉以指向一個大局。
我對台灣政治圈尤其是人渣圈熟透熟爛了,對我而言,圈子裡絲毫不存在任何意外,幾乎沒有任何會讓我感到驚訝之事。
察覺事物於未發之時,那是先知先覺,例如林毅夫、范光棣,李光耀、伏爾泰、羅素及維根斯坦等等,而我只是後知後覺。至於絕大部分人則是不知不覺,其中為數最多的當然就是腦殘。腦殘之中還有救的我看頂多只有百分之一。
後知後覺者也許有點義務應該關注一下那些不知不覺者。
哲學的第一課就是epistemology,大凡對哲學有點興趣的人難免在這第一課上產生困惑,例如我為什麼能知道事物?我如何產生想法,形成信念?我怎麼會知道一加一等於二?我受傷了,我怎麼會知道是我在痛而不是別人?我怎麼會知道這是我的手?這一切都顯得很奇怪不是嗎?
無此困惑者,請走它路,哲學之路顯然與你無關。
小可愛昨天突然問我說:把拔,你說你研究ㄧ加一等於二,一加一等於二是以前的人發現的嗎?如果都已經知道答案了,還要怎麼研究?
我還沒有機會好好回答她,我只跟她說,看起來越是簡單的東西,其實更神秘不是嗎?
羅素是數學天才,卻得花上幾百頁才能推導出一加一等於二,而我們一兩歲就知道答案。問題是,重點不是答案,甚至不在於我們究竟怎麼知道答案,更是在於為什麼會有ㄧ加一等於二這回事?
我問小可愛說,在高雄,一加一等於二,在上海等於多少?她說還是等於二。我再問,如果是在劍橋呢?她說還是二。我接著問,如果是在宇宙的某個角落呢?ㄧ加一還是等於二嗎?小可愛遲疑了,搖頭說她不知道。
我當然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些無可懷疑的定理,似乎更是疑雲滿天。沒有這些困惑者,那恭喜你了,你根本不需要浪費時在哲學上。
我不是要講數學哲學,而只是很納悶:為什麼這哲學的第一課–epistemology似乎從來不曾讓大部分人感到困惑?人們認知事物與概念總是如此自然,自然得跟機器人好像差不多,不過就是輸入一些程式與資料,他就會如你所願地思維與言行。
我這樣講其實有點侮辱了機器人的智慧,難道你輸入與結論相反的資料,AI還是會照樣喊抗中保台,捍衛民主自由?我想應該沒有這麼固執的機器人才對。這當然也顯示出人類果然還是高機器人一等,我們有怪異認知,AI應該比較不會有。不過,這還能叫做認知嗎?這還是epistemology的管轄範圍嗎?也許它應該放在 “病態性認知” 裡頭,就跟精神病的妄想差不多,無法以理性與感性來理解。
我覺得某個意義上腦殘很像鸚鵡。鸚鵡會說話,表面上是人話,其實是鳥話。在人類的現實中,鳥話無法從現實之中獲得它應有的意義。鳥話就是鳥說的話,跟人話頻率不同。維根斯坦有句名言:”獅子即使會說話,我們也不知道牠在說什麼”,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你可以教一個腦殘說出任何你要他說的話,但你沒法說它是經過一套認知程序而來。你甚至沒法說那是一種信念,而比較像是一種妄想,一種delusion,或頂多像一種台詞,無法對應到任何現實。
哲學上有一道著名的爭議,是Thomas Nagel提出,叫做,”當一隻蝙蝠是什麼感覺?”
我相信,就算我們能够在肉體上完全改造成跟蝙蝠一樣的認知或感知功能,恐怕都還不足以說是當一隻蝙蝠的感覺。
我也常納悶,當個腦殘到底是什麼感覺?有沒有可能我也是腦殘,但我自己並不知道?
我們家如果養一隻鸚鵡,我猜,在小可愛和小月亮的薰陶下,氣質會下降,很可能會滿口 “屁啦”,”滾啦”,”你白痴喔”?
小時候,我家旁邊的台南保安宮養了三隻鸚鵡,其中有一隻每天都會喊蔣總統萬歲,我可以說這隻鸚鵡很愛國嗎?另一隻比較浪漫,會唱情歌,只會一首,歌名叫做 “梅蘭梅蘭我愛妳”,是當年的流行歌。第三隻安靜無語,像哲學家,經常呆呆看著宮廟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