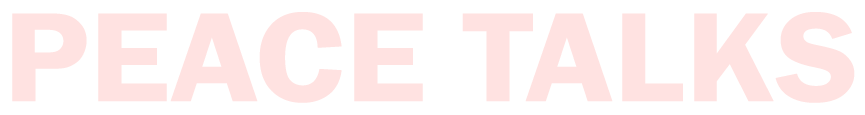人生可憫
人生可憫
陳真
2025.07.08.
我其實還沒回應德宣。我知道我在想什麼,可卻寫不出來。我若寫這樣,人們一定會以為我在說那樣。表達能力是我一生最大的殘障。
黃文雄刺殺蔣經國失敗後,匿蹤逃亡26年,直到法律追訴期已過才現身。
1996年,黃文雄剛回台灣時,據說只有陳菊知道他的下落,於是我就打電話給菊姊,請他轉告黃文雄說我想見他。
幾天後,我就接到黃文雄的傳真,我從台中去台北接他,忘了當時彼此是怎麼相認。他送了我一本Roy Bhaskar的Critical Realism當見面禮。
後來我們很常聯絡,我每個暑假都會從英國回台灣看門診賺錢,有幾次就住在他家,跟他同床。他好像習慣全裸睡覺,要我也全脫,但我敬謝不敏。
有一次,我找了一些護士和學生來跟黃文雄認識,地點就在他家。那天晚上,我們十來個人圍成一圈在他家陽台聊天。我提出一個深藏我心中許久的想法。
我說,林義雄遭受滅門血案是人間至痛,但是一般人的生活所遭遇的各種痛苦,事實上並不亞於林宅滅門血案之痛。
我說原因有三,一是痛苦很主觀,當事人說有多少痛就有多少痛,一隻甲蟲之死的痛苦,不會亞於巨人之死。
原因之二是林義雄是無數人尊敬的人格者,台灣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長年以來,整個社會,甚至包括國民黨支持者,統統給予林義雄無數的關懷、溫暖與安慰。
可是呢,一般人卻只能默默承受所有痛苦,根本無人知曉,無人在意。你若不識相,偏要把痛苦說給人家聽,往往只是自取其辱,別人會覺得你大驚小怪無病呻吟。
比方說,我有個失眠憂鬱的病人,是個七、八十歲的慈祥善良老阿嬤。她有兩個兒子,一個是重度精神分裂症,一個長年吸毒與坐牢。
在吸毒兒子出獄期間,精神分裂症那個兒子,把吸毒且有家暴問題的另一個兒子給殺了,被判重刑。
我的病人除了以淚洗面,世界上除了我,根本沒有任何人願意理解她的痛苦,更不用說為君垂淚了。
在我看來,這樣的痛苦,遠比一個眾所週知的名人被滅門更可怕,更可悲,更痛苦。
原因之三是,為了某種正義而犧牲,從而廣受尊崇,眾人以淚相伴,那樣的痛苦難道會比一個家庭小孩吸毒、對母親家暴、手足相殘更痛苦更可怕更可悲?
如果只能二選一,我寧可選擇前者而非後者,因為前者是榮耀的,完全是可理解的,而後者卻全是難以啟齒的恥辱與慘劇,難以言喻的病態,毫無尊嚴可言。
但是,黃文雄顯然不認同我的想法。不過,他認不認同不重要。今天,我如果不曾經歷或體驗一般人無可言喻的地獄之痛,也許我也不會對千千萬萬個普通人的生活寄予深情。
林義雄第一次發起反核千里苦行時,我是很積極的核心參與者,貢獻了很多心力。
當千里苦行走了一個多月即將走到終點時,可以預料隔天在終點處必然會有大批群眾夾道歡迎。
於是,當隊伍即將走到終點站的前夕,林義雄請我幫他擬一個講稿,我答應了,於是馬上在路邊利用休息時間就開始寫。
稍後,林義雄又來問我,我的講稿主題是什麼?我說很簡單,就四個字:”苦行不苦”。
我跟他說,我們的所謂苦行,每天走累了就住免費高級大飯店,吃喝全是雞鴨牛羊盛宴。我說,如果苦行是一門職業,恐怕會有幾百萬人來應徵,因為實在太爽了,哪有苦可言?
我說,在苦行途中,幾次遇到路邊一些工人和農夫看到我們在大太陽底下苦行,冷冷地嘲諷說 “你們真的是吃飽太閒”。他們的嘲諷並非沒有道理。
林義雄聽完我的 “苦行不苦” 的說法後,開心地大笑,用英文說,Good idea!
我想說的約莫就是這個意思。至於馬英九,他受過什麼苦?有著什麼了不起的情操與貢獻?值得為他抱屈呢?
我也很喜歡他,但他所承受的痛苦,遠遠不及一般人的千萬分之一。
我把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最愛的父母全都奉獻了,而我至今除了依舊承受永無止境的誤解抹黑嘲諷威脅恐嚇和鄙夷羞辱之外,我有得到什麼公正的評價嗎?周圍熟或不熟,識與不識的同事、同學或同行,有幾個人對我是尊敬的?大多愛理不理或鄙夷不是嗎?
有了小可愛之後,我常感後悔,如果我能夠正常一點,不要那麼排斥光鮮亮麗,不要那麼排斥功名與地位。如果我也來當個什麼部長或院長,我如今還會帶著小可愛四處鞠躬哈腰,卻依然哀哀無告求救無門嗎?往往極盡卑微地寫上千百字求助,不過只是問對方一些臨床問題,有多少人不是很不耐煩地用兩三個字回覆我,隨便打發?
其實不用說當行政院院長或內政部長衛生署長什麼的,光是當一個議員就足夠橫行無阻了不是嗎?
記得在高醫見習時,有一天,一位議長還是議員,發燒感冒了,院方馬上安排住院,高醫院長還親自來幫他量血壓,成立醫療團隊,只差沒幫他擦屁股。他媽的不過只是小感冒,卻照顧得無微不至。
我不知道別人看不看得懂我所要表達的?對此我很懷疑。我並不是說我也想要特權,我更不是說我需要什麼回報,我只是想說,我總覺得,就如沈從文所說,生命可悲,人生可憫。
我也常想到我創立的兒童福利協進會的座右銘,取自羅曼羅蘭的一段話:
“只要有一雙真誠的眼睛陪我們哭泣,我們就沒有為生命白白受苦。”
這回在哈爾濱我給自己買了一個手搖的音樂盒,一個才十幾塊錢。我買它是因為它上面寫了一行字:
“愛你,我從來不遺餘力。”
我對家人,對世界,盡棄所有,毫無保留。
我還在哈爾濱中央大街某家店看到一個小玩意,上面寫著:
“你若記得,我便活過。”
我指給小可愛看,她說她看不懂,一直要我解釋意思。我說,不用解釋,也許有一天妳自然就會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