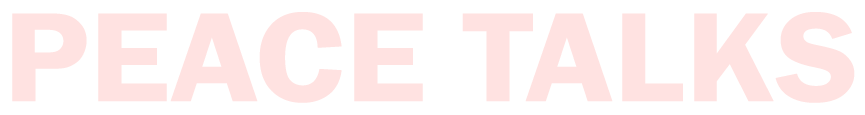我的忘年之交
我的忘年之交
陳真
2025.09.28.
講到柏楊,講點八卦,不過這和世界和平無關。
柏楊1977年出獄,出獄後兩年,我就認識他了。起因於他寫的一篇文章,提到說發燒會把腦子燒壞。
因為柏楊早年的雜文集經常鼓吹我們應具有科學理性精神,應就事論事,不怕權威,不和稀泥,於是我就寫了一封信請報社轉交給柏楊。
我在信裡說,柏楊先生您說錯了,發燒不會燒壞腦子,因為我們大腦有個調控體溫的中樞,不會燒壞腦細胞。腦子如果壞掉,是因為病原體或發炎所致,而非體溫。
柏楊很快就回信了,他不服氣,認為是我觀念錯誤,還詢問我的生物老師的名字,說要找他糾正,希望他別誤人子弟。
柏楊很溫柔,很幽默,沒大沒小,老少咸宜。但他很熱情,個性有點倔,有點孩子氣,似乎還有點衝動。許多時候,我彷彿在他身上能看見自己的影子。
於是我們ㄧ老ㄧ少就開始這樣一來一往地通信。柏楊大我四十幾歲,他那時候應該快60了,而我還是個高中生。
柏楊出獄後,娶了第五任太太張香華,她是我在建國中學高一時的國文老師,只教了一小段日子,溫柔婉約,聲音動人。
準備上大學那一年的夏天,我常去台南市長榮路一家圖書館看書,裡頭有很多平常看不到的禁書。有一天,有個大約二十幾歲工人模樣的男子走過來,找我搭訕。他說,”同學,你怎麼會看這種書?” 我記得當時正在讀前衛出版社的一本叫做 “自由主義” 的書,殷海光的學生林毓生寫的。
那個來搭訕的人自我介紹說他就是這間叫做 “功能圖書館” 的主人。這圖書館不收任何費用,甚至採良心制,無館員監督,只需自行登記,便可以把書借走。
他說這圖書館是他自掏腰包所成立,每個月薪水不過兩萬多,長年省吃儉用,希望多買些好書來推廣。他認為人民的文化素質很重要,比政治本身還重要,所以窮一己之力,立志推廣知識。
我把這事告訴柏楊,柏楊聽了很感動,於是就說他可以商請出版社不定期寄一些書送給我們。柏楊也把他寫的各種新書或舊書,經常會寄送給這間圖書館。柏楊還介紹我認識一些作家,請他們贈書。
我和柏楊除了通信,也偶爾打電話,他告訴我很多往事,常讓我在電話的另一頭熱淚盈眶。
他幾次邀我去他家作客,但我始終不曾赴約,幾十年從未與他見面。為什麼呢?因為我加入黨外,風波不斷,威脅不斷,殃及父母,常感覺心裡很疲憊。再加上極端貧窮,實在沒有多餘的金錢和心力特地從高雄跑去台北新店找他。
不過,這些其實都是次要因素,真正讓我裹足不前不願受邀的原因是,我覺得,跟一個自己所尊敬的人相處,就維持這樣一個距離就好,走太近往往容易起變化,維持一個美好的感覺與不遠不近的距離似乎最好。
1997年,我去英國求學前夕,寫了一篇公開信刊登在許多報章雜誌上,題目叫做 “不捨夢想,告別台灣親友”。柏楊看到這封公開信,於是寫了一封信來,信裡說,他覺得我有點多愁善感,希望不要太糾結於個人的痛苦與受難。他說,歷史上無數的人,曾經遭受遠遠比我們還要更巨大的痛苦,付出更大的代價。我們個人這麼一點痛苦,實在不算什麼。
他還寄來一張卡片,記得上面寫著:”以筆為帆,祝你一路順風”。
出於忙碌,我沒有回信,而這也是我跟他的最後一次聯絡。
十年後,2007年,我返台定居,第一個想見的人就是柏楊,但因為忙於照顧病重的父親,心力交瘁,ㄧ夕白髮,遲遲沒有行動。隔年,2008年,柏楊就過世了,在我心裡留下一個很深的遺憾。
柏楊和范光棣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們待我如知己。他們的過世,似乎也帶走我心裡深處一些東西,經常感到特別寂寞,彷彿再也沒有什麼人在乎我了。
我這輩子寫了四十幾年,幾千萬字,一大半束諸高閣,另一半就貼在自己的幾個留言板上。
不管寫了多少,我心裡從未有讀者的存在,即使是關於現實世界的文字,也只是自己寫給自己看,就像自言自語那樣。
當一個人自言自語時,他心裡空空蕩蕩的,彷彿這個世界跟他沒有一點關係。當他自言自語時,旁人即便聽見了,他其實也沒有意思想講給誰聽。
我沒有一絲發表慾。范光棣過世前,一直急切聯絡我,說要幫我出書。他說,只要我點個頭,他可以幫我包辦一切,尤其是出版那些從未發表的哲學筆記。
但是,儘管他再三勸說,我還是沒打算出書,這不單純是因為寫得好不好的問題,更是因為我實在不想跟這個世界有太多瓜葛。尤其是在我父母過世後,似乎帶走了我每一個明天,只剩餘生,再無前路。
父母的離去,讓我覺得自己似乎更少了一些虛榮,卻多了更多的寂寞,原來孤兒就是這樣一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