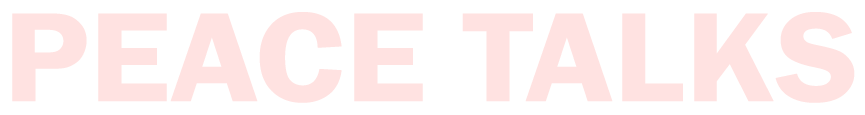關於什麼數位中介法(3)
關於什麼數位中介法(3)
陳真
2022. 08. 26.
台灣戒嚴長達38年,列入金氏記錄。在戒嚴令底下,聚眾抗議者是唯一死刑罪。所謂聚眾就是三人或三人以上聚集,所謂惟一死刑,指的是該項罪名只有一種刑責,一種判決,那就是死刑。
八零年代,當我 (們) 在這樣一種恐怖高壓下反抗蔣家的戒嚴體制時,面臨的不只是黑牢,更是性命難保。現在的人大概很難想像為何走上街頭和平抗議之前需要先寫下遺書,交待好後事,大概也很難想像為何喊出一句 “抗蔣家” 必須要有必死的決心。不曾挺身而出者,不可能–注意我的措詞,我說的是 “不可能”–不可能想像決心迎向死亡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你不妨想像眼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平安路,啥事也不會有,甚且前途輝煌,另一條則有著一把槍指著你的頭,膽敢再往前一步,就要你的命。請問你走哪一條?當你選擇了順服的平安路時,請你捫心自問,你真能體會選擇死亡之路者是一種什麼樣的決心與感受嗎?
哲學上我常藉助一個詞來表達某些想法,那個詞叫做holism。中文不知道怎麼翻譯,意思大約就是:”意義” (meaning) 必須隸屬於某個整體而無法單獨獲得。
好比說車馬炮,車直行,馬拐腳,炮翻山,它們之所以擁有這些行走功能是因為它們隸屬於棋局。一旦抽離了祺局,它們便失去棋局底下應有的意義。也就是說,事物本身並沒有某個必然的內在意義,它們的意義得從其所隸屬的整個系統中來取得。
也許所有概念都是這樣,隸屬某個家族;你沒法光談某個概念卻把其所屬的家族丟一旁。
我反戒嚴抗蔣家時,當時生活中極少數不把我看成壞人的人,他們很友善地勸我說,”你幹嘛要反戒嚴?戒嚴礙著了你什麼?” 他們還說:”我愛怎麼講話就怎麼講話,很自由啊,根本不會有事啊”。
我跟他們說,”你們當然不會有事,因為你們的思想與言論根本就是統治者所灌輸、所歡迎的,怎麼可能有事?” 但我不一樣,我的言行思想對統治者是有威脅性的,因此,我連在學校考卷上填上西元紀年都會被視為 “反中華民國” 的罪證。
人渣黨掌權之下,目前不會有大規模殺人關人的作法 (以後就不好說了),不過,法西斯的本質與蔣家是完全一樣的,全盤掌控了媒體與教育,透過謊言長期洗腦,透過抹黑栽贓、起訴、排擠、剝奪資源與阻礙前途就業與孤立等等各種懲罰與報復手段來對付極少數拒絕臣服者。
比起蔣家,人渣黨之惡有過之無不及。為什麼呢?因為蔣家畢竟是為了圖謀整體社會秩序與大多數人利益的穩定性,但是人渣黨卻純粹就是漢奸台奸,純粹就是為了一己私利而寧可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企圖在不久的將來犧牲絕大多數人的性命與身家財產。
不過,我在此並不是要講這個。我想說的僅僅是:為什麼你會以為什麼數位中介法將會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呢?事實上,島內根本從來就沒有過言論自由不是嗎?
你之所以以為你有言論自由是因為,就如同我上述所說,你的言論基本上根本就是統治者所灌輸、所歡迎的不是嗎?例如什麼反共,例如什麼抗中保台,什麼民主自由,什麼台灣主權等等等,人渣黨長年以來不就每天洗腦你這些鬼東西嗎?
至於極少數屈指可數的異議者,我們之所以還活著,之所以還沒有遭到更大規模更慘烈的懲罰與報復是因為,整個媒體與教育完全掌控在人渣黨手裏,你的聲音根本沒有多少人聽見,起不了多少作用。
當有一天,出於某種因應時局變化的政治需要,這項懲罰與報復的規模與力道就會加重,什麼數位中介法就是這樣一個產物與手段,為將來美國隨時可能挑動的兩岸戰亂預做準備。
我想說的是,什麼數位中介法將來很可能還是會通過。就算它沒通過,事實上我們還是一樣從未有過什麼言論自由。如果你以為你有,那只是因為你的想法與言論與當權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是無害的,無關痛癢的。
我看一些親綠勢力也在抗議什麼數位中介法,感覺很好笑。你們哪需要擔心?你們絕不可能會是被整肅的對象。這個法是衝著島內極少數希望兩岸和平或希望兩岸統一的人而來。
一如holism 所提示,如果你真的在乎什麼數位中介法,那你就更應該在乎其所屬的整個惡質法西斯體系,一群無惡不作無所不貪的人渣歹徒,在美國的收買與豢養底下,當其走狗,徹底控制島內整個媒體與教育,幾十年來每天鋪天蓋地用無數謊言顛倒是非黑白,洗腦大眾,腐化下一代心靈,讓其認賊作父,鼓動骨肉相殘,為美國人賣命,為美國人殺害自己的兩岸同胞。
所謂言論自由,絕不是一個什麼碗糕法,而是一整個權力系統,一整個體制,而這樣一個體制,由過去蔣家年代的反共,二十多年來被美國推展到不光是反共,而是仇中反華,腐化下一代仇視自己的文化與血統,一來仇中去中,斷其文化命脈,二來反華,作賤自己的血統,說自己的血統是一種骯髒邪惡的 “支那賤畜”,教導下一代去跪拜真正傷害與殺害我們數十萬同胞的日本與美國。
如果你不在乎這樣一種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法西斯殖民體制,卻僅僅在乎什麼數位中介法,其實只是自欺欺人,就如同我不可能僅僅只是在乎車馬炮的走法,卻根本不在乎我們究竟是在下著一盤什麼樣的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