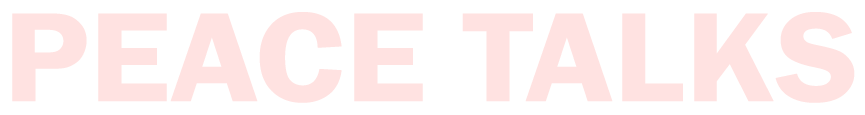我永遠不會成為哈瑪斯
我永遠不會成為哈瑪斯
陳真
2023.12.15.
昨晚深夜才剛抵達長沙,一大早在睡夢中接到電話,小可愛又生病了。現在馬上得趕回台灣。
平常只要有電話來,必然就是有不好的事發生,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從無例外,從來不曾有好事。只要電話響,我就心裡顫抖,非常害怕,因為只要有電話來,就是災難又來了。
這幾十年來,幾乎從未接過一通告訴我某個好消息的電話,或是至少是和平與平安的電話。
實在受不了這種精神折磨,宛如驚弓之鳥,隨時擔心家裡或親友出事。
因為周海媚之死,最近報紙一直在講紅斑性狼瘡的事,不斷提醒,看了很難受。
小可愛診斷仍然不明,但是病痛不斷,幾乎沒有一天例外,沒有一天是沒有各種病痛的。
升上三年級之後,老師卻認為她是裝病,儘管我兩個月來不斷寫了上萬字詳細陳述病情,老師還是不相信世界上有這種什麼自體免疫疾病,甚至對她進行全班公審,全班霸凌與羞辱,說她就是裝病,所以才遲到(每星期約遲到一至兩次次,每次遲到約5分鐘)。
不得已只好緊急轉學。
最近兩個月我幾乎都沒睡覺,日夜不停處理臨時多出來的各種災難事件,包括處理霸凌與轉學爭議,以及處理我的叔叔中風與失智一年、天天吵鬧及轉院與安置的事,實在痛苦不堪,極度疲憊。
人活著就是艱難。俗話說,自古艱難惟一死,我覺得這話是錯的。我不覺得個人死活 “本身” 有何困難可言?殺頭不過是風吹帽,敢在世上逞英豪。如果不是為了家人,死活根本一點都不可怕。
世上最可怕最艱難的是你沒法好好照顧家人,你甚至得眼睜睜看著家人受苦。
念小學時,老師不敢在我面前體罰同學。每次老師們要揍人,要打那些功課不好的同學,就會叫我離開教室,不要看,因為只要看到同學被打的痛苦表情,我的眼淚就會像斷了線的珍珠,無聲無息地不停落下。
我常懷疑自己是不是有什麼毛病,為什麼我就是沒辦法看到哪怕是一個陌生人的受苦,彷彿他的傷也就是我的傷,他的痛,也就是我的痛。
下個月的一月二十三號,就是我承受這一切艱難的21週年紀念。21年前的1月23號的凌晨三點,就在我剛剛跟指導教授慶祝完我終於解決了關於 Cora Diamond 和 James Conant 所提出來的關於所謂nonsense所產生的內在概念矛盾問題時,那一天晚上,同樣是在睡夢中,我接到越洋電話,說我爸爸中風倒下。
21年來,我花了十年不眠不休的照顧,送走了父親,送走了我大哥。我大哥肝硬化,就在我已經準備好要開刀要把我的肝臟捐出一半給他的前夕卻過世了。
送走父親與大哥,接著是學姐開刀失敗,醫生沒縫好血管,導致術後多天卻突然大出血,失去心跳呼吸血壓,失去生命跡象,我透過CPR硬把她從鬼門關救了回來,休養了一年。
接著幾年後,我又送走了同樣是肝硬化的二哥。
接著就是我的叔叔,失智,中風,一生未婚,身無分文,膝下無子。
每次總是在於我以為一切病痛災難總算遠颺,生活似乎開始要從一團恐怖火焰灰燼中重生時,另一個災難馬上又會來臨。
我更是從沒想過,恐怖惡疾竟然會發生在自己的小孩身上。我面對的,將是一場與病魔更為艱難的戰鬥,直到可預料之年歲老去以及不可測的那一刻疾病結局的悲劇到來。
最近兩個月,在極端痛苦與疲憊之中,我給自己賦予一個任務:
平常只要有哪怕只是幾秒鐘的一點點零碎時間,我就收集以色列這回不太掩飾的大屠殺直播。
老實說,我從來不曾看過那麼多男人哭泣。對於這些為人父與為人母者,我覺得自己其實就是他們的一份子。我沒法幫他們什麼,但我想記下、留下他們的痛苦。
你可別以為這與你無關,事實上,我所記下的淚水,一如汪洋,裡頭也必然有著屬於你、屬於每個人的一滴淚。
在這個意義上,我知道我永遠不可能成為哈瑪斯,我永遠不會希望有人經歷我所曾經歷的這一切。因為我知道,即使是殺子仇人,當他的小孩或親人受難,他事實上也一樣屬於這片淚之汪洋。
我們理應是一家人而不是仇人,只是我們往往遲至悲劇之後才發現彼此不分你我。畢竟誰能分得清大海裡頭無盡汪洋之中的這滴淚和那滴淚究竟屬於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