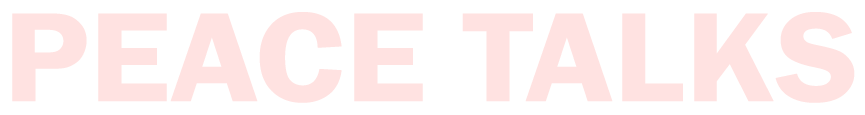欲知世上刀兵劫
欲知世上刀兵劫
陳真
2024.11.27.
這跟世界和平好像沒有關係,它似乎只是長年以來在我方寸之間的一道道烈火之痛。但是,如果它跟世界和平沒有關係,為何它卻產生如同戰爭烽火下婦孺被屠戮般的悲痛?
當醫生最痛苦的事之一,除了目睹生離死別與他人罹患惡疾之哀痛之外,莫過於它。它產生如此巨大的折磨,無能改變它之餘,許多時候讓我有一種連一秒鐘也待不下去的感覺,很想脫離,就像脫離黑幫那樣一種心情。
那麼,它究竟是什麼呢?很難描述。也許可以說,就是一種冷血,一種不屑,一種任意可為之、完全不需任何原因的霸凌。反正病患就是弱者,我愛怎麼整你就怎麼整你。
許多時候,我很想問問這些霸凌者:這位病患是妳的殺父仇人嗎?這位生了病連一張健保卡都拿不穩的阿嬤,是跟妳有奪夫之恨的仇家嗎?如果不是,為什麼妳要這樣吼她整她,處處跟病患站在所有需求的對立面呢?病患連他有什麼疑問或需求或病痛都還沒開始講,為什麼妳就馬上說辦不到,叫他滾呢?
今天,有個八十幾歲的阿嬤,看完診之後隔一段時間,又回頭來我診間敲門,有疑問想問我。
阿嬤行動不便,隻身前來就診。她也許不夠淑女,敲完門後就直接推開門,於是有人馬上暴跳如雷,怒吼叫她出去,說醫生在忙。
那時沒病人,我哪有在忙?於是我就起身趕緊招呼阿嬤進來。怒吼者就更生氣了,一番怒斥,阿嬤受到驚嚇,佇立門口,不敢進來,我趕緊又再用力招呼,請她進來。
怒吼者很生氣,但我畢竟是她的上司,不敢攔阻,於是容許阿嬤進來。
我知道阿嬤聽力不好,於是趕緊挪近椅子,招呼阿嬤挨著我,坐到我身邊。
她拿出一些我開給她的藥物,準備開口詢問,才剛講兩個字,那個人竟然衝到她身邊,在阿嬤耳邊大吼,叫她閉嘴,大罵說我們還沒有允許妳講話。
我當下就跟那個人說,為什麼妳這麼兇呢?阿嬤到底做錯什麼?那個人看到向來溫和得像小貓咪的我居然也會質疑,於是才悻悻然回到座位上,停止怒吼阿嬤。
這類事情,充斥四處,我經常跟院方反映,但沒有效,到最後也只能忍。
對於病痛者,我們主動盡一切努力去幫助人都來不及了,怎麼反而好像病患全是我們霸凌的對象或仇家似的,完全就是站在病患的對立面;仿佛若不對立,就是寵壞了病人或被病人佔了什麼便宜似的。
許多時候,人心離得很遠,但是戰爭卻很近。其實何止醫院,就在生活周遭,我彷彿都能經常看到血肉模糊,聽到炮聲隆隆,聽到無聲的悲痛哀嚎。任何人,似乎只要有求於人,或是在某些方面成為弱勢,馬上就會成為別人任意無情踐踏與虐待羞辱的對象。
這跟世界和平沒有關係嗎?如果人心如此,戰爭與奴役便永難止息。
佛教有一偈語,如是我聞:
“千百年來碗裡羹, 怨聲如海恨難平; 欲知世上刀兵劫, 但聽屠門夜半聲。”
我並不是要談所謂動物權,我不想成為任何所謂社運的一份子,不願給自己貼上任何標籤。因為我想要說的東西無須任何概念的型塑與鋪陳,它甚至不需理由,根本無須思索。
我愛天上的雲,地上的花花草草,我愛小孩的笑容與無知童語,這不是因為我對它們進行過一番思索與概念型塑之後的結論,這只是像微風拂面一樣自然的東西。
今天晚上,小可愛因為某些事而意志消沉,悶悶不樂。我跟她說,妳想不想聽我的一個秘密?她馬上點頭,因為她最喜歡聽秘密。於是我就裝神弄鬼凑近她耳邊說:
這是關於我自己擁有快樂的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其實我很早就已經告訴全世界,但我不知道有幾個人相信。希望妳最好要相信。
然後我就在小可愛的耳邊,把秘密告訴她。
她笑了,覺得我在裝神弄鬼搞笑。她可能覺得這哪算什麼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