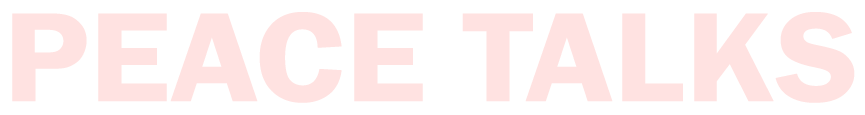像狐狸又像刺蝟
像狐狸又像刺蝟
陳真
2022. 08. 24.
我在心理上常有一種強烈的抗拒去說明某些想法,不光是因為它們本質上難以(用通俗語言)說明,而是因為那樣一些說明往往於事無補,缺乏實用價值。說到底,許多時候我畢竟是個實用主義者。就好像面對一台影印機,你只要學會怎麼操作就行,至於它背後的什麼靜電原理、光學成像原理,那就不干一般人的事了。
通俗有個俗字,聽起來好像矮了一截。理論有個理字,感覺高尚許多。其實,高低之分,duck不必。許多時候,我還挺看重通俗,看重實用。我過去有幾篇英文的文章談維根斯坦的哲學本質,就是賦與它這樣一種性質,簡單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那就是pedagogical(教學的)。
維根斯坦生前寫了一兩千萬字筆記,相當可怕,數量跟我有得拼。但他其實翻來覆去不斷在講同樣的一兩件事,就像一本說明書那樣,反覆說明某一台機器。維根斯坦自己的說法是,他覺得自己就像個導覽員或傳教士,用各種不同方式反覆介紹同一個東西。
我的文字也有兩種,其中一種是不需要聽眾的,專注於真理,專注於一己之思,就好像企圖找到某個數學定理始終都不需要聽眾一樣,你根本不用去管聽眾的反應,聽眾是愚或智,統統與你所專注之事無關。
真理該有多少難度就任它有多少難度,微積分該當如何便如何,而不需要為了讓聽眾聽懂而改變訴說方式。降低難度。
另一種文字就得考慮聽眾的感受和理解方式了,因為它是pedagogical。簡單這麼說:我得努力想辦法讓聽眾們聽得懂才行。即使是個三歲小孩,我更得想辦法去理解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到底是怎麼看待世界的,我得想辦法用他所能理解的方式反覆去教他,看能不能讓他從不懂到懂,從妄想或胡思亂想到真實信念。
我本來是要寫所謂言論自由,但覺得累,覺得煩,總覺得講這些東西的內在性質其實很荒涼,很無謂,寫來又臭又長。在某種意義與用途上,我們只須懂得如何操作影印機就,至於它背後的原理,那就不干一般人的事了。
我很討厭市面上一種約定俗成的集體態度,比方說講到什麼言論自由,就講得好像什麼不證自明的寶貝似的,講得好像它不是人工產品,而是長在樹上的果實那樣自然,甚至還說什麼100% 純天然呢,講得煞有介事,非常反智,難以與言,聽了實在很無奈。
當眾人把什麼言論自由講得如此天然美妙時,你若不折不從,彷彿就不文明不道德了似的。
其實呢?最野蠻的原始人時代,言論自由肯定最充份,他愛說什麼就說什麼,自由百分百。可是,那是野人,不值得羨慕。文明人才不會想要什麼100%的言論自由。要不,難道你可以每天用幹你娘問候你的老闆?或是為他畫一幅性交圖,看你能維持多久的100% 言論自由?幾年前,法國興起一波全球性的所謂 “我們都是查理” 的傻社運便是如此。千萬可別算我一份,我才不是查理,我沒那麼沒水準。
你能瞎掰說飛機上有炸彈或在電影院大喊失火嗎?當然不行。特別是當麥克風根本就掌握在敵人手上時,言論自由基本上就是一種骯髒透頂的思想恐攻武器。
古希臘有一則寓言,狐狸想盡方法想吃刺蝟,哪怕使盡千方百計還是吃不到,刺蝟就只會一招,但那就夠了,於是產生這麼一句諺語:「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
從這寓言的上下文來看,顯然刺蝟模式是高出一籌的,比較厲害,很多人於是就以刺蝟自況,以示思想不凡。但我覺得,我們為什麼不能像狐狸又像刺蝟呢?沒必要二選一吧?我上面說的兩種文字,一是專注於真理型,一是通俗於教學型。前者無須聽眾,後者卻得心懷天下人,若在島內,尤其要心懷腦殘。
腦殘真的是有福了,哈巴狗電台是他們的,為他們而存在,為他們而發出一點微小但篤定的光芒。
反之,真理則不需聽眾,更不急於訴說;畢氏定理就算晚三千年發表,依然真理。維根斯坦曾經說,沒有人會去在乎康德的寫作究竟是寫於兩百年前或五百年前。誠哉斯言。我們抬頭看著滿天繁星,感動之餘,大概也不會在乎星子們真理般、詩一般地存在,究竟是存在於三億或五億年前,一樣燦爛。
但是,教學文字不一樣。它是為聽眾而存在、而想方設法的。真理惟一,但教學方法卻千千萬萬,千千萬萬個方法全指向那惟一的東西。因此,我們一方面得像個刺蝟,只拜一神,只談一局,只見一個世界。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也同時狡猾得像隻狐狸,一會兒說這樣,一會兒講那樣,花樣多,方法多,目標卻只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