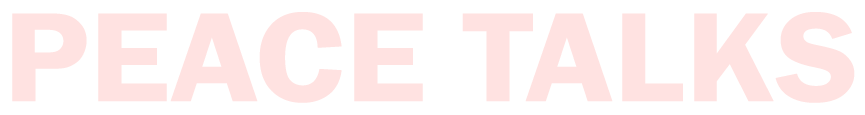悼念一位我無緣認識的同學
悼念一位我無緣認識的同學
陳真
2024.06.28.
今天,帶小孩去給一位同學看診,同學告訴我,班上一位女同學自殺身亡。
在我印象中,這位女同學豪爽,活潑,直覺上是個性情中人。但我知道,也許恰恰是這樣的人反而容易深藏死志。
她的死,讓我很難過。我這一生,經歷的生離死別並不少,但她的死卻使我心情瞬間沉到谷底。
我對自己的難過感到意外。我為什麼會如此難過呢?事實上,大學七年之中,我從未跟她講過一句話。我甚至不太確定她長什麼樣。我離她最靠近的一次距離至少10公尺以上。
那天,應該是1986年的9月30日星期二,也就是民進黨建黨的兩天後。我去上課,一走進教室,感覺全班同學們的異樣與不屑眼光彷彿像一束束強光那樣,從四面八方照射而來。
有位男同學大聲拍桌怒斥,對著其他同學說,”政府為什麼不把這些人抓起來!” 接著,有位來自金門的女生,遠遠地瞄了我一眼,大聲說:”我看他(指的就是我)就像共產黨!”
說這話的女生,就是這位自殺身亡的女同學。
憑著識人的直覺,我其實一直對她深具好感,總覺得她是個好人。
她對我的不屑與厭惡,我並不是那麼難過,也許是因為我的四面楚歌基本上就是一種長年至今的常態。當時整個校園裡,幾乎沒有人願意正眼看我。平常在校園走著,同學們迎面走來,幾乎全是鄙夷或視而不見,就像過街老鼠那樣,人人厭惡。
許多時候,有些同學甚至還會把我攔下,英勇地對我羞辱唾罵一番。高醫七年,悲歡一場。
全校同學們對我表現厭惡表現得最為具體的一次遭遇是,有一天,應該是1984年,我在高醫的學校餐廳裡,單槍匹馬散發自己寫的一份反蔣家的黨外文宣。
就在我散發傳單時,突然有人悄悄走到我背後,迅速拉開衣領,把一碗滾燙的熱湯倒進我的衣服裡。我當下疼痛難堪,非常狼狽。
在場用餐的各系男女同學們卻紛紛笑開懷,敲桌鼓譟,歡呼了起來,為這位往我身上倒入一整碗滾燙熱湯的同學歡呼叫好,彷彿他英勇地消滅了共匪似的。
在那個年代,在台灣人的普遍認知與主流敘述中,黨外、台獨與共匪是完全可以畫上等號的所謂三合一敵人。
這些校園遭遇,相較於槍炮黑牢的實質威脅,相較於身為黨外連累父母的各種慘烈政治報復,其實是相當微不足道的,但我卻一直深深記得那位女同學對我充滿不屑的鄙夷眼神。
雖說微不足道,但難免沮喪。我只能在心裏告訴自己,也許五年八年,也許三十年五十年,也許總有一天,人們會相信我並不是一個貪婪之徒或卑鄙壞人。我只是無法壓抑心裡的某種感情,從而奮不顧身,以命相許。
也許誤解澄清的那一天永遠都不會到來,也許我註定得一生遭受誤解與屈辱,但我早已認命。一個人的個性與情懷,事實上就是他給自己寫下的命運篇章。
我常覺得來日方長,總有一天將如何如何,可惜時光飛逝,來日並不方長,往事並不如煙。
我以為一些人與事並不急,事實上逝去的種種,已然逝去。
我很想問問同學們,她的埋骨之處呢?她還有哪些家人?跟她熟識的人不妨多告訴我一些關於她的事,有沒有什麼是我能為她做的,讓我在心裡深處為這樣一個無緣認識的同學,挪出永遠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