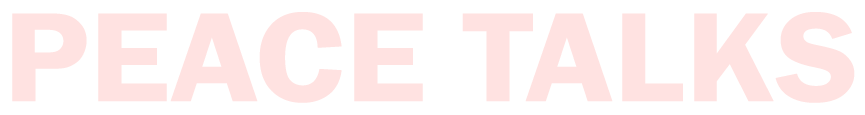良善社會的存在基礎 (1)
良善社會的存在基礎 (1)
陳真
2022. 09. 01.
(續)
造謠很容易,澄清卻很難,為什麼呢?因為:
一,你很難證明你根本沒有做過的事。
比方說阿扁就住我家隔壁,我如何證明我不曾偷看阿扁洗澡?
二,謠言四處擴散,但你卻不可能追得上其擴散速度與範圍,你不可能去跟每一個人澄清,你甚至根本不知道謠言如何蔓延擴散?
三,大多數人不會去細究是非,而只會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接收主流媒體的聲音。
四,對於受害者當事人而言事關人格與榮譽的極端重要之事,對於旁人來說卻不痛不癢,這意思是說,人們對於是否誤解了受害者並不在乎;你的清白對他來說只是身外事,根本不影響他的生活,因此他並不在乎自己是否輕易聽信謠言。
綜合這幾點因素,人渣們當然會非常熱衷於造謠抹黑,因為只要敢於無恥,要人格謀殺任何一個人都太容易了。人渣們並不需要人們完全接受謠言,他只需要讓人們覺得你充滿道德爭議,他就贏了。這時候,你的人格就已受到摧毀。
幾十年來,人渣黨最擅長的就是造謠抹黑這一招,無往不利。
其次我要說的是什麼叫做邪惡。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很多違法的人,事實上一點都不邪惡。哪怕是殺人放火也一樣,他當然違反了法律,但在道德上卻不一定卑鄙。
反之,很多並不違法或違法程度並不高的言行卻十分卑鄙齷齪,充滿邪惡心機。抹黑張善政抄襲之事便是一例。
沈富雄說,張善政太老實。他說,這是張善政得分的好機會,他卻不懂得把握,只會傻傻地澄清他根本沒有做的事。
昨晚下班後,打開電視,剛好聽見沈富雄說,會說張善政抄襲的人,根本就是台語說的 “不識字兼不衛生”。這句台灣俚語的意思是指一個人沒受過多少教育,低俗而愚蠢。
沈富雄說,張善政應該藉這個機會把民進黨打扁才對,讓大家知道民進黨這些人有多麼 “不識字又不衛生”。
沈富雄其實很狀況外,他應該沒有什麼被抹黑的經驗,所以才會這麼 “單純”。他應該不知道,31 年前當他返台在機場被捕時,我肯定是全台灣惟一一個積極去營救他的人。
國民黨抓沈富雄,脫離不了政治懲罰的動機,因此以他攜帶禁藥入境謀利的罪名逮捕,同時還放出謠言說他身上還夾帶著手槍。那時候我剛大學畢業,在台北長庚和林口長庚醫院工作,馬上幫他發起醫界連署,要求釋放,要求公開透明的審判。
我拜訪或書面寫信連絡了各大醫院至少一百多個醫生,包括沈富雄過去在台大的一些同學,結果只有一兩個人願意公開具名聲援,絕大多數人都推三阻四。
我並不是要求大家聲援沈富雄無罪,而只是要求不要黑箱審判,不應以政治為由,故意入人於罪。但是,幾乎所有人都還是不願具名,只敢私下罵國民黨惡質。有些人甚至酸言酸語,落井下石。落井下石是很卑鄙的,但是明哲保身也不是什麼高貴的品格。
除了膽小之外,其實主要原因是人們根本不在乎你沈富雄是否真的夾帶禁藥入境販售謀取暴利,也不在乎你是否還攜帶槍械。在很多醫生的口中,”你沈富雄一定幹了一些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否則怎麼會被抓?警察幹嘛不來抓我呀?”
在那當下,沈富雄該怎麼澄清自己根本沒有做的事?又該去跟誰澄清?澄清有用嗎?人們會信嗎?人們會花時間去研究你的案子與為人,從而相信你的清白嗎?當然不可能。這就是抹黑的威力。
沈富雄說,只有那些 “不識字兼不衛生” 的蠢材才會說張善政抄襲。這樣講其實太高估一般所謂讀書人了。其實,一個人如果不曾從事學術研究,恐怕不一定能夠理解抹黑張善政抄襲有多麼荒唐。就算是醫生,我看一大半的醫生應該連這樣的鑑別能力也沒有,因為台灣醫生接受一種很僵化的臨床教育,跟學術研究沾不上多少關係,很多醫生應該連什麼是學術研究都不清楚,更不用說一般沒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了。
張善政那篇報告的寫作方式,基本上就是四處蒐集某個主題底下的相關資料。他在第一頁就寫了他的方法就是透過一些關鍵字去搜尋國內外的相關論文或報章雜誌的文章或報導。全篇報告就算沒有一個字是張善政寫的也不是問題,因為該報告原本就只是要蒐集各種相關資料。這跟它媽的抄襲能扯上什麼鳥關係?
就比方說我有個檔案,非常龐大,是關於貧鈾彈之健康傷害的各種論文、報導或報告,少說也有好幾千頁,是我過去二十幾年來所關注的成果。這幾千頁的檔案,僅有幾篇文章是我自己寫的,還曾應邀掛名某篇我或多或少參與了一點意見的學術期刊論文,其它99.99%都是別人寫的東西。
如果有人願意花五千萬來買,我可以考慮賣給他,二十幾年的心血,五千萬並不貴。如果有人說我這個關於 “貧鈾彈之健康損害” 的數百萬字檔案乃是抄襲而來,那他就是腦子進水了。這是一個像資料庫那樣的檔案,跟他媽的抄襲能扯得上什麼鳥關係?
人渣黨的邪惡就在此。人渣黨裏頭總有些學者吧,有可能連這樣也不懂嗎?但他卻偏偏故意列舉許多文字,然後告訴大家說 “你看你看,這裏抄,那裏也抄,到處抄”。
真的很卑鄙,故意混淆兩種完全不同類型不同本質的文字,故意把學術論文跟這類型的文獻資料報告混為一談,讓完全不懂學術或疏於做研究的人誤以為抄襲。
這個黨真的是邪惡下流到爆,故意魚目混珠來減少對於人渣黨選舉的傷害,故意把完全不一樣性質的兩種文字混為一談,故意把一種旨在進行文獻資料收集的報告,和那個什麼堅及什麼阿通師狼狽為奸全盤抄襲騙學位的假論文做為一種相似性的類比,好讓大家誤以為什麼堅的就算抄襲,張善政抄得更嚴重,甚至抹黑他藉此詐欺斂財騙取公款。
知道我在說什麼的,不用我說肯定也知道這樣一種空穴來風之抹黑的齷齪與荒唐。原本不清楚的,經我這麼一說,實際上我也不知道你是否清楚了?或者是其實你並不在意他人名節,是非如何對你根本無所謂?
我覺得,人們最好要有所謂而不要無所謂,因為我相信,一群在乎是非善惡的人民,也許才比較有可能建立起一個比較正直良善的社會。當我根本不在乎受害者的人格名節時,有一天當我受害,我憑什麼希望人們能夠在乎我的冤屈與痛苦?如果大家彼此之間都不在乎彼此的冤屈與痛苦,你想,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三十幾年來,我跟沈富雄只見過幾次面,就只曾在醫界聯盟的第一屆執委會上一起開過幾次會,他至今連我是誰應該也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三十幾年前他落難時,有個剛畢業的醫生花了多少心血企圖營救他。
在那樣一個政治高壓年代,我之所以願意那樣做,並不是因為我和沈富雄有任何私交,而只是因為我在乎是非,在乎受害者的感受。這樣一種在乎,也許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某種文化素質,型塑了正直良善社會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