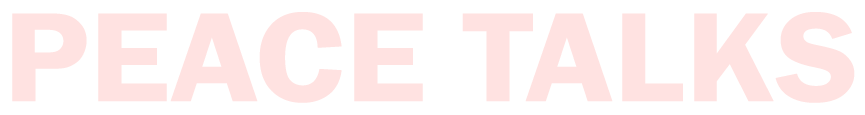典範轉移已然到來?(1)
典範轉移已然到來?(1)
陳真 2023.11.24.
這兩年社會上有句口號大家朗朗上口,叫做 “下架民進黨”。這個人渣黨,不值得一提。而我想說的是,下架國民黨,恐怕比下架人渣黨更重要。所謂惡紫之奪朱,偽君子的危害,勝於真小人。
Thomas Kuhn 有個流行術語叫做paradigm shift,中文翻譯做典範轉移。意思是說,一個已成典範的科學理論往往不太會變動,就跟一種戰略一樣,通常是很長久的事,會變動的是在這個具有戰略地位的理論底下的各種枝枝節節。
可是,當許多反證、異例不斷出現,當典範的某些核心概念逐漸難以因應異例的挑戰時,當它到了某個時間點,我們就只好放棄這個典範。
做為民進黨的建黨黨員,其實建黨的隔年(1987年),我看這個黨開始賄選買票包娼包賭,我就想退黨了。有一天,我告訴陳菊說,我想退黨。陳菊說,現在黨才幾個人,都已經快沒人了,你還要退黨,那不是打擊大家的士氣嗎?
於是,一直拖到1994年的228那一天,我才正式退黨。那時候我退不退黨其實已經無關緊要,因為那時候的民進黨早已經是掠取功名利祿之捷徑,無數蟑螂老鼠投機文人搶著入黨,裝模作樣喊喊口號,搶著分一杯羹。
其實,早在退黨之前,也就是大約1990年之後,我就再也沒有投票給民進黨。陳定南是惟一一個例外,我不但投票給他,我還幫他助選,寫文宣,甚至站台演講。
除了陳定南之外,我至今不曾再投票給民進黨。不過,我退黨前後那幾年還是持續投給綠營,例如當時無黨籍的郭倍宏。
也就是說,即使是1994年正式退黨之後,我還是依然支持綠營。一直到什麼時候我才決定 “典範轉移” 呢?一直到1998年,當民進黨在美國的指令下,開始喊出 ‘’愛台灣‘’ 的法西斯口號,開始進行仇中反華的族群挑撥時,我很痛苦,因為那已經跨越道德底線,那意味著,我不只是退黨而已,而是從今以後,這個我所參與建立的黨,已經成為我的敵人。我不只是應該退出它而已,而是應該消滅它,讓這樣一個已經癌化、已經對台灣社會產生致命傷害的政黨,掃入歷史灰燼的垃圾桶,以免危害整個台灣社會。
儘管國民黨過去傷害我甚深,從1998年到現在,我的每一張選票都還是投給國民黨。不管再怎麼爛的國民黨候選人,我還是照樣投給他。因為我知道,黑金老賊李登輝之後的新國民黨,再怎麼爛,還是遠遠勝過骯髒齷齪無恥下流貪婪無度無法無天到極點的民進黨。
我想說的是,我相信,另一個典範轉移的節點似乎也已然來臨;從今爾後,我們應該斷然拋棄國民黨,因為它似乎已經質變到一個已然無法回頭的轉捩點。
在某個根本意義上,它已經變成一個小民進黨。我指的根本意義,就是指的殖民定位的本質。它已經不折不扣就是一個完全被美國所操控的傀儡,完全聽命於美國,並且被美國欽定的人馬所徹底掌控。
有些人也許仍然寄望於未來,寄望於比方說洪秀柱或張亞中等人,將來也許能夠把國民黨拉回正軌。我不敢說毫無可能,只能說我個人缺乏信心,因為,至今為止,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對美國說一聲不,全都裝啞巴,更不用說公開挑戰美、日對台灣的殖民,對台灣的無盡剝削,對台灣的掠奪與傷害,對台灣的往戰火裡推。
如果所有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對美日根本連屁都不敢放一個,你還能寄望它什麼?
我倒也不是寄望柯、郭等人。如果他們結盟,我這一票也許會給他們,但我之所以支持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敢對美國說不,而是因為他們畢竟不是美國的規劃人選,自主性多少還保留一些,尤其是郭台銘,以他的自身利益而言,他應該是最不想看到戰爭的人,同時也是唯一一個敢公開說要兩岸和談並且要求外國勢力退出的政治人物。
上個世紀末,我公開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一封告別信”,告別與我私交甚篤的所有綠營同志,從今爾後,我們不再是同志,而是敵人。
我原本交遊滿天下,在那之後,直到今天,幾乎沒幾個朋友。在我發表那封告別信之後,我斷然與所有昔日綠營友人斷絕往來,直到今天,差不多二十五年來,感覺自己就像孤魂一樣,生活中沒幾個朋友,政治上更是徹底成為一個異類。
1995年,我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我的叛亂案也隨之終於畫下句點,我終於被解除境管,允許出國。
1997年的七月一日,我飄洋過海來到英國。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其實有,但我還不太會用),我是帶著一台用六千元買的打字機出國。出國前夕,我利用醫院的藥品處方箋列表機,把我的通訊錄一一打字,然後列印下來,準備帶出國。足足列印了幾乎一整天,我數了一數,我的同志與朋友一共2700多個人,幾乎涵蓋全台灣絕大部分的政治與社運參與者。
我始終沒想到,我1997年出國,帶著將近三千人的好友名單,隔兩年,差不多1999年,我就跟這三千同志就此告別,化友為敵。因為我知道我不可能當一個漢奸或台奸,我不可能去和法西斯狼狽為奸,我不可能昧著良心傷害台灣及兩岸同胞,我不可能出賣靈魂充當邪惡美日帝國的走狗。
天大的利益與權力都不可能讓我去幹這些事或是對之裝聾作啞。就算把我抓去刑場槍斃,我也不可能違背良心。
1997年,我出國前夕最後一個單獨相處的友人及同志就是林義雄。他長年善待我們,我出國時他還給了我一筆錢,至今我還保留著那張支票的影本留念。
我出國後的隔年,他就當上了民進黨黨主席,整個黨開始炒作 ‘’愛台灣‘’ 的法西斯口號,製造內部敵人,看誰與對岸親近,看誰對台灣不忠,醜化外省人等等等。
1997年,我出國前夕,在許許多多的媒體與報章雜誌上發表了一封離台赴英的公開信,叫做 “不捨夢想”。那時候的我,充滿對台灣未來的抱負。當時,我非常看重林義雄創辦的慈林基金會。位於宜蘭的慈林圖書館,在它都還沒打下地基、剛開始要整地時,我就已經去了現場好幾趟,給這個地方拍照,留下許多影像紀錄。我在黨外十年所擁有的幾乎所有重要錄音帶、錄影帶與歷史文物及雜誌等等等,全都捐給當時八字都還沒一撇的慈林圖書館。
1997年出國前夕,我去找林義雄,告訴他我對將來的許多理想與打算,我希望將來能夠來慈林工作,希望慈林能創辦一所人文性質的學院,我願意用一輩子全心投入,在這所未來的慈林學院,我希望它能效法胡適時期的 ‘’中國公學‘’ 那樣的治學精神,不以文憑為考量,聘請真正的良師來教學,求真求實崇尚美麗與良善。透過這樣一所學院,希望能給台灣社會帶來一點點好的影響。
我沒想到,短短兩三年的時間,我的這個夢想便瞬間化為泡影,昔日情同手足、情同家人的同志好友們,倏忽全部來到了對立面,只剩下星星點點的三、五好友,其中一位就是良哲。
聞曲不難,成為曲中人卻十足艱難。任憑千百折磨,任憑家破人亡,個人永遠難以對抗一種集體圖謀。相較於歷史上那些英雄烈士,這麼一點個人滄桑實屬微不足道。個人之力卑微渺茫,但是,無數的個人,以各種不同形式的付出,其實還是能改變整個大局。
中國百年屈辱,被洋人與鬼子血腥糟蹋到何等地步,如今還不是又站了起來?所以,也許我們無須太悲觀。一顆星,就儘管兀自閃爍。一朵花,就好好開出一朵花的模樣。也許有一天,滿天盡是繁星,整座山便開滿了花。
小可愛前幾天問我說:“把拔,你做這些事到底有沒有用?” 我跟她說,妳看天上那麼多星星,有一些星星很燦爛,有一些星星跟我們一樣,微弱得幾乎看不見,但它還是一樣在那很孤獨很遙遠的黑暗中閃耀著一點光芒,直到它生命的終了。它不會老想著有沒有用,然後就不閃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