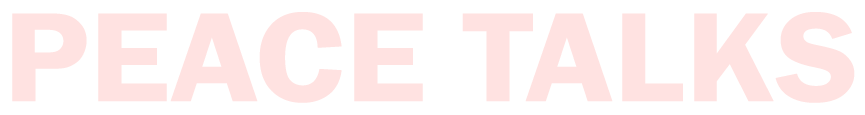范光棣與我(1)
范光棣與我(1)
陳真
2023.01.23.
1月23日是個悲傷的日子。20年前的今天,我接到越洋電話,說我父親病倒,我從此又走入另一段坎坷人生。但我並不是刻意挑在這一天來寫這文章,純粹是巧合。
范光棣幾天前過世了,就像一盞熄滅的路燈,沒有引起世人的絲毫關注,島嶼更不知道自己喪失了什麼。
我也許不是一個好的哲學家,但我識人也識貨,我知道人之所以為人,知道作品好壞是怎麼一回事,套一句范光棣關於維根斯坦的論文標題,我能理解 “范光棣的其人其文”。
四、五年來,他經常要我帶著小孩去拇指園看他,但因為某些緣故,始終未能成行。小孩知道范爺爺幾次簽名寄來一些童書給她們,卻從未謀面,如今天人永隔。
幾年前,范光棣中風,聽他說,中風之後只能使用”一指功” 打字,很吃力,但仍然寫作不斷。他還告訴我說他事先網購了一種安樂死的藥物,打算有朝一日自我了斷。我回信請他告訴我藥物名稱以及何處可購得,我說也許有一天我也會需要這款藥物,用在自己或家人身上。
在他健康持續惡化之際,有一天,他卻寫信來說要幫我出書,我說我不要。幾次推辭之後,他仍執意想要說服我,強調只要我把檔案全寄給他,授權他處理,他就能親自幫我把書一本一本出版,完全不需要我花一點時間。我告訴他說,重點並不是在於我有沒有時間,而是在於我不覺得自己的思想與文字有什麼值得出書的客觀價值;它們具有某種個人意義,但我不喜歡看到它們變成一種廉價商品供人品頭論足。
2012年–我之所以清楚記得是因為我父親就是在這一年過世–大陸有個雜誌社編輯寫信來,說想邀我寫一些關於我和范光棣的文字。這個雜誌社叫做 “讀者”,據說是大陸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之一。他們之所以找上我是因為,他們看我曾寫文章提到說我這輩子除了對不起父母與家人之外,最對不起的一個人就是范光棣,雜誌社因此想請我把相關故事寫出來。
我並沒有拒絕,但我回信說,很多事情很微妙很個人很唯心,因此也很難表達,也不知道要從何說起。
在幾次通信中,我約略提到為何我最對不起的一個人就是范光棣的原因。雜誌編輯說,如果我同意,光是我寫的這些信件就值得直接刊登出版。
收到雜誌社這樣一封信之後,我卻從此直到今天都一直沒有回信,因為就在那時候,我多次中風臥床十年的父親過世了,我消沉了很長一段時間,完全不想與人連絡,同時也寫信告知各方學界與醫界友人,辭掉各種職務與課程及演講,表明我從今起不再上台講課或演講,也不願受訪。
整整十幾年的時間,我根本不知道范光棣人在哪,更沒有任何連絡。但是,大約是2016年之後的某一天,突然來了ㄧ通陌生電話,我沒接,對方持續來電,我還是沒接,後來他在電話中留了言,竟然是范光棣。他在留言中說:“我是范光棣,你跑去哪裡流浪了?我很想念你。”
於是,我們就聯絡上了,而且還去拇指園讓他招待了兩天,說不完的話題,全圍繞著美國與法西斯民進黨之惡行昭彰以及祖國的偉大復興,還提到他當年和中共幾位領導人的往事歷歷。我對什麼量子力學的興趣,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這幾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絡,我知道他也很想知道為什麼我一生最對不起的人是他。他後來約略知道一些來龍去脈,但強調自己是老子思維,並不介意,也要我別把這些小事放在心上。他常說,他覺得我的個性很像維根斯坦,難怪我這麼喜歡維根斯坦。
表面上,我對不起他的那些事確實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過就是他在離開哲學界二、三十年之後,卻因為我而破例接受劍橋的邀請,從台灣特地來到劍橋發表一場閉門演講,我是惟一受邀者,但我卻因故而沒有出席。
他在演講前一天,送給我一份演講前一天才寫的手稿,裡頭開宗明義提到說,做為哲學界早已銷聲匿跡幾十年的 “恐龍”,他之所以願意接受邀請前來演講,就是因為我。
我是在演講結束幾天後才去讀這份演講手稿,方才知道他做出接受邀請的決定竟是如此意義重大,而我卻辜負了這樣一個信任。我原本以為,不過就是一場演講,完全不知道他之所以願意應邀復出是因為我的緣故。
據說現場的與談者還問他說你演講中所提起的那個對哲學想不開的劍橋學生怎麼沒有來聽你演講?還開玩笑說他們可不會因為研究維根斯坦而真的放棄哲學。
范光棣後來知道原由之後說他並不介意我沒有出席,同時也叫我別把這小事放在心上。
表面上也許是小事,但是,我活這麼大半輩子,從未承受如此的信任。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我身上或文字中看見什麼。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純粹就是兩個陌生人,他只讀過我用中文寫的一篇五、六百字短文,叫做“維根斯坦與我”。
托爾斯泰曾經說:”如果有個女人,心甘情願為你煮一頓飯,你該死而無憾”。二十幾年前,范光棣對我這樣一個陌生晚輩所做的,卻不僅僅是”煮一頓飯”,但我卻渾然不覺而輕忽以對。
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做為一個一生飽受誤解與屈辱及極端貶低的人,沒有比理解與信任更罕見的事了。
謝謝范光棣,希望我配得上你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