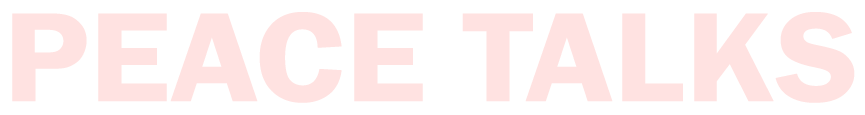喪心病狂的日本鬼子
陳真
於上海
2023.08.25.
小日本這個國家真的是骯髒無恥透頂,連核污染整個海洋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居然也幹得出來,存心當人類公敵。以後大家連吃個海鮮都可能罹癌。
連日本人自己也在抗議,整天喊反核的台灣人渣黨與綠色生物們卻像日本鬼子養的狗那樣乖巧。
這個曾經在我國姦殺擄掠殺害上千萬同胞,並且幹下人類史上完全泯滅人性的無數邪惡暴行(例如731部隊)的邪惡國家,不但竄改歷史,從不認錯,毫無一絲羞恥心,甚至至今還繼續抹黑並傷害我國,百般挑釁,危害人類,無惡不作。
這樣一個邪惡國家,有什麼資格繼續存在這個世界上?至今甚至還不斷在台海挑釁。
我常納悶,日本人難道真的沒法體會人性?難道他真以為自己可以幹盡邪惡之事卻不會點燃仇恨與報復?
如果有一天,日本鬼子再度攻擊我國,難道他們不曾想過我們對日本人將會有多麼巨大的仇恨爆發?日本人顯然以為只要當美國人的小跟班就能繼續為所欲為,繼續無惡不作。
我對日本這個國家與民族性很了解。他們膜拜力量,膜拜拳頭,膜拜強者,至於善惡是非,對這個國家與民族來說,似乎不值一個屁。誰拳頭大,他就舔誰,日本人打心底看不起弱者,一心跪拜強者。你要他道歉悔過,門都沒有,除非你徹底把他打趴在地,他就會叫你阿爸,就像美國人對他的種種傷害與打壓,包括在他根本已經是強弩之末時硬是還要賞他兩顆原子彈,他不但不以為忤,卻反而跪喊著美國爸爸。
他再繼續對我國傷害下去,我看有一天,他很可能也要喊中國爸爸。
=======
日本核廢水排海 港專家呼籲3類海鮮以後少吃
2023-08-24
聯合報
記者謝守真
日本24日開始將核汙水排海,香港專家呼籲,以後最好少吃鮪魚等三種海產。(中通社)
日本於台北時間24日12時開始排放核廢水,香港政府決定於同日起,禁止源自東京等10個都縣的水產品進口。香港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主席梁美儀則建議香港市民,以後三種海產最好少吃為妙。
據香港商業電台報導,梁美儀批評,日本政府將核汙水排海的做法不恰當,是要其他國家跟著做「人類大實驗」。他指出,日本所有相關報告都只強調放射性物質氚的濃度符合標準,但未提及其他高劑量輻射的核元素,這樣是在誤導大眾。日方難以完全經稀釋程序消除所有核元素,排放入海的汙水對自然和人類仍然有害。
梁美儀建議香港市民,即日起應少吃大型魚類,如黑鮪魚,每年最多吃一、兩次即可。他解釋,這類魚屬食物鏈高的生物,會吸入不同汙染物,或對人體有害。
此外,海床泥土易有汙染物沉澱,且汙染濃度較高,因此他也建議,要少吃比目魚等底棲性魚類,以及貝或蚌類等會過濾水中有機物的水產。
日本將排放核廢水的消息,已經影響香港民眾吃日本料理的意願。有香港日式餐廳負責人無奈表示,自日方宣布24日啟動排海後,有過半數已預約的客人要求取消訂位。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董、日式餐廳負責人陳強說,餐廳生意自日本宣布排放核廢水後已下跌10至20%,最近跌幅擴大至40至50%。
========
反制福島核污水入海 大陸封殺日本水產
2023-08-24
經濟日報
記者謝守真
綜合報導
大陸宣布24日起暫停進口所有日本水產品,反制福島第一核電廠排放核汙水決議,雙邊緊張情勢再度升溫。
(歐新社)
日福島核汙水昨(24)日排海,大陸海關總署同日發布「關於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的公告」,稱為全面防範日本福島核汙染水排海對食品安全造成的放射性汙染風險,保護中國大陸消費者健康,確保進口食品安全,依據有關規定,決定即日起全面暫停進口原產地為日本的水產品。
對於大陸封殺日本漁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4日傍晚表示已提關切,要求中方立即撤除禁令。
大陸外交部24日批評,稱日本政府無視國際社會的強烈質疑和反對,單方面強行啟動福島核事故汙染水排海,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這一錯誤行為。
大陸外交部指出,日本福島核汙染水處置是重大的核安全問題,具有跨國界影響,絕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文章寫到,自人類和平利用核能以來,人為向海洋排放核事故汙染水沒有先例,也沒有公認的處置標準。
大陸外交部指稱,日本政府沒有證明排海決定的「正當合法性」,沒有證明核汙染水淨化裝置的長期可靠性,沒有證明核汙染水數據的真實準確性,沒有證明排海對海洋環境和人類健康安全無害,沒有證明監測方案的完善性和有效性,也沒有同利益攸關方充分協商。
陳真
發佈日期: 2023.08.25
發佈時間:
上午 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