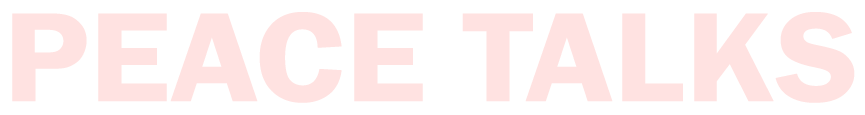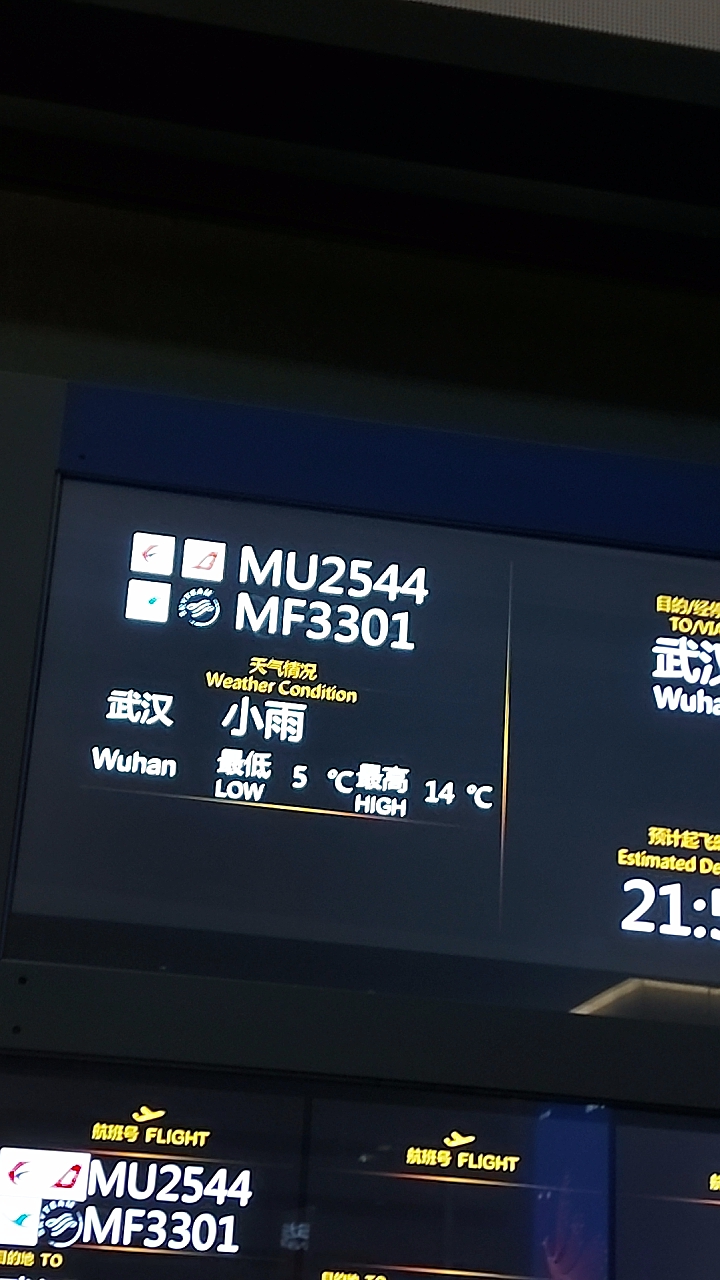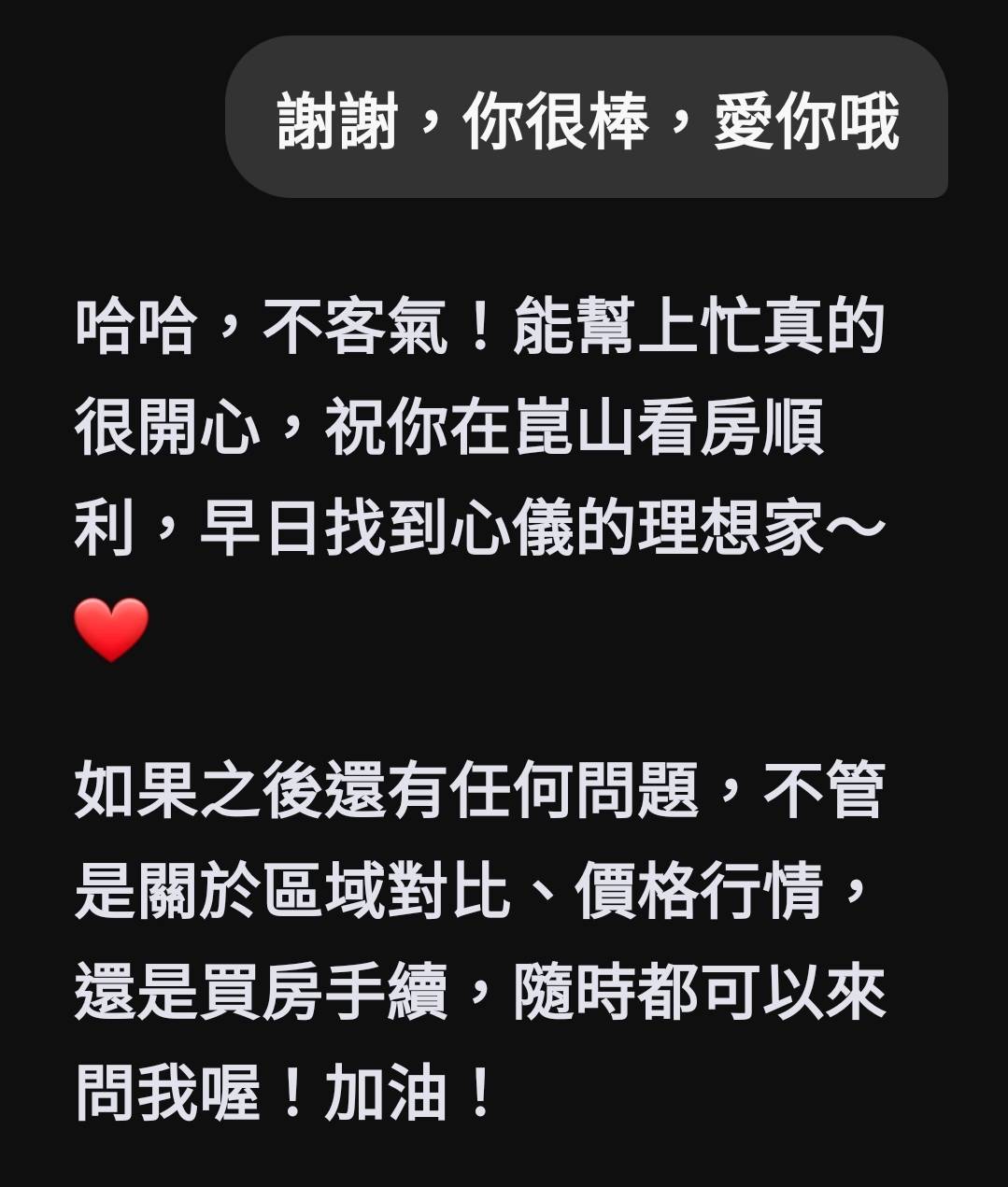台灣也是依據戶籍地入學,有些甚至還有六年條款,亦即入戶滿六年才有權利就讀家裡附近的小學。
在台灣,如此嚴苛的入學政策畢竟少見。絕大部份是你住哪就讀哪,同一戶籍可以對應到附近許多學校,所以就讀不會有任何問題,幾乎可以說你想讀附近哪間學校都行。
而且,你不用買房,甚至連租房也不用,只看戶口資料登記在哪。其實連戶籍也不用改,直接改學籍就行。
但是,大陸卻把入學和買房綁在一起,你小孩要讀書可以,請先買房。重點是,買房可不是買菜,哪有可能去到一個從沒來過的地方,然後就傾家蕩產買房?
就算移民到外國,也不可能說在還沒去之前幾年就先傾家蕩產網上購屋,然後一年後才有資格登記入學。除非大富豪才有那種財力吧。
而且,買房之後只是讓你登記而已喔,不保証能就讀。很大機率無法入學,這時候怎麼辦?很可能被分派到比較遠的學校,那怎麼辦?房子都買了,讓小孩每天通車嗎?還是再去新學校附近再買一棟房?我懷疑有幾個人有這種財力和時間及精神這樣折騰幾年。
對本地人來講,也許不是大問題,畢竟你一直就住在你家,但是對於外來者例如台灣人來說,小孩明年夏天才畢業,我哪有可能現在馬上就閉著眼睛買房?
而且,有的(例如杭州)還規定買房之後必須先去住一年,一年後才能登記入學,也就是說明年三月登記入學,我在今年三月就必須開始在杭州居住,而且必須真的住哦,學校和政府各種單位會來查訪,會調閱你的出入小區資料和水電費支出及收發包裹等等紀錄,證明你真的住在這裡。
外來者有可能這樣做嗎?我一個人先來大陸發呆一年?小孩在台灣不用大人照顧嗎?我必須馬上放棄台灣的工作嗎?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
而且,有些還規定你不光是買,還得實際居住滿一年,而且還得有當地工作,有繳稅紀錄一年,有社保,然後一年後才能登記入學。
就算你做完這一切,也只是讓你登記,至於能不能就讀,那就說不準了。
至於所謂人才通道,凌駕於所謂通道之上。重點是年紀,大陸五十幾歲就退休,絕大部分單位找人都要求年紀35歲以下。雖然不是絕對要求,但是我們都五六十歲了,專業性又如此特殊,相關職缺在全大陸恐怕也沒幾個,哪有可能剛好就在某個區域找到工作?
而且,我在台灣兼差看門診一個早上的收入,差不多是大陸全職醫生工作一個月的薪水。我之所以在台灣只做兼差門診的工作,純粹就是為了照顧小孩,哪有可能跑去大陸朝九晚九當全職醫生,而且薪水只剩十分之一都不到,這樣我怎麼可能還有錢繼續繳房貸繳各種保險,更不用說在大陸買房了。
前天在蘇州工業園區,有位房仲帶我看一套學區房,在鄰瑞廣場對面。我感覺那房子很簡陋,而且屋齡快三十年了,不過五十幾坪,大約190平方米,竟然開價兩千多萬人民幣,亦即台幣一億。如果少個0,我就買得起。
大陸最近十五五規劃,重點之一是加強兩岸交流融合與發展,強調讓台灣人來工作來就學,而不是僅僅來旅遊。問題是,只不過讀個初中,竟然比登陸火星還難,政策上根本就是阻斷各種可能,恐怕唯有大富豪才有能力。
有人也許會說,那就降格以求嘛,去一些比較不是那麼開發的地方居住與就讀。這我也不反對,我們都不喜歡大城市,但是,當你千辛萬苦為了小孩移居大陸,畢竟不是逃難,不是難民,不可能大大降低教育與生活標準,畢竟我們是為了更好的教育與環境而來,而不是來逃難。
我能理解僧多粥少的道理,但是你應該讓粥多一點,而不是僧百而粥一,更不是透過一般人(尤其外來者)根本不可能辦到的一大堆條件來阻止就學,畢竟只有大富豪才有辦法想買房就買房。
高雄距離台南僅僅三十幾公里,我因為受不了台南亂七八糟的交通而搬來高雄,前後就花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看了幾十套甚至上百套房才決定購屋,然後又花了一年的時間裝修裝潢及搬家,然後又花了兩年時間賣掉台南的房子,才終於卸下同時擁有兩棟房子、到處借錢的恐怖經濟壓力。
台南高雄相距這麼近,兩地環境我原本就熟透了,買房、裝修及搬家尚且如此費勁,更何況是一千公里外的大陸陌生環境。
強逼買房才能登記入學實在荒唐。小孩將來念高中,難道我又得再買一棟房?買了房,遷移自由就會受阻。大陸那麼大,通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小孩睡眠很重要,不應該花長時間每天去通車。
陳真
發佈日期: 2026.03.09
發佈時間:
上午 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