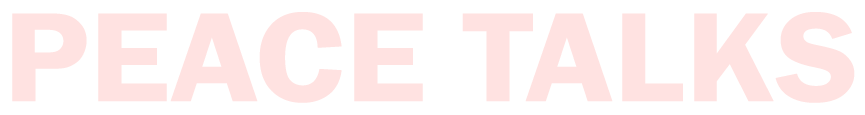To quote Wittgenstein, 竊竊私語可能比較貼近我說的意思,畢竟沒有人會公開談情說愛給大家看,就跟任何形式的禱告一樣,你知,天知,再無他人參與,純粹是你跟對方之間的事。
留言須知:* 欄位為必填,但Email 不會顯現以避免垃圾郵件攻擊。留言時,系統會自動轉換斷行。
除網管外,留言需經後台放行才會出現。絕大多數人留言內容不會有問題,但實務上無法把大家全設為網管,以免誤觸後台重要設定,還請舊雨新知見諒。
2169 則留言。
我覺得.... 如詩
稍微切分排版,不知道有沒有誤解您的意思
我深信,我是能說服人的
你的跟我的,心跳,沒有兩樣
能讓我熱淚盈眶的
在你心中
也該
激起一絲惆悵
我沒有意圖說服任何人
正因這毫無防備的坦誠
你才可能
真正地
見我所見
信我所信
但我的說服方式比較慢
家教,戀愛
只能是一個靈魂
對另一個靈魂的
低聲耳語
我無法對著十八雙眼睛
同時啟齒
至於慢
那是哲思的本質
傳遞一個事實
只需一瞬
但若要遞給你
一整個觀看世界的法門
一片我棲居的星空——
那就急不得
正如梭羅的惆悵:
我不奢望說服這一代人
但我或許,是你孫子的
渴望
~
非常温暖的采访,奶奶96岁,思维和表达,都很顺畅。
家人逐漸失智,看了很有感慨。
https://youtu.be/UZ4yuhYgBAY?si=BofPWuxM1v7mgNsf
~
当时看直播,在胡同里很随机的一次采访却是出人意料的精彩,特别是中天小姐姐走的时候,奶奶说“我这辈子上你们那去不了”,瞬间泪奔
~
领导来看望,老奶奶不想聊的时候,还“扭过脸儿去”,实在是真实又有趣
~
天啊,这个奶奶不一般,老人家提到前北京市长蔡奇的时候经常去看望她,这可是大领导,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
中天小姐姐的这次随机采访,也给台湾朋友进一步的了解到了真实大陆和共产党员,体现出了大陆的官员无论多大的官真切的对待普通老百姓平易近人,处处想着人民
~
小姐姐只是打招呼时说了一句台湾中天电视,奶奶临走还记得,说明脑子非常清楚。非常有爱的采访。
~
共產黨對高齡黨員都是有關懷的 逢年過節都會去拜訪的 送個米麵油 看看家裡有沒有困難 困難老百姓也會拜訪的 是尊重
稍微切分排版,不知道有沒有誤解您的意思
我深信,我是能說服人的
你的跟我的,心跳,沒有兩樣
能讓我熱淚盈眶的
在你心中
也該
激起一絲惆悵
我沒有意圖說服任何人
正因這毫無防備的坦誠
你才可能
真正地
見我所見
信我所信
但我的說服方式比較慢
家教,戀愛
只能是一個靈魂
對另一個靈魂的
低聲耳語
我無法對著十八雙眼睛
同時啟齒
至於慢
那是哲思的本質
傳遞一個事實
只需一瞬
但若要遞給你
一整個觀看世界的法門
一片我棲居的星空——
那就急不得
正如梭羅的惆悵:
我不奢望說服這一代人
但我或許,是你孫子的
渴望
~
非常温暖的采访,奶奶96岁,思维和表达,都很顺畅。
家人逐漸失智,看了很有感慨。
https://youtu.be/UZ4yuhYgBAY?si=BofPWuxM1v7mgNsf
~
当时看直播,在胡同里很随机的一次采访却是出人意料的精彩,特别是中天小姐姐走的时候,奶奶说“我这辈子上你们那去不了”,瞬间泪奔
~
领导来看望,老奶奶不想聊的时候,还“扭过脸儿去”,实在是真实又有趣
~
天啊,这个奶奶不一般,老人家提到前北京市长蔡奇的时候经常去看望她,这可是大领导,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
中天小姐姐的这次随机采访,也给台湾朋友进一步的了解到了真实大陆和共产党员,体现出了大陆的官员无论多大的官真切的对待普通老百姓平易近人,处处想着人民
~
小姐姐只是打招呼时说了一句台湾中天电视,奶奶临走还记得,说明脑子非常清楚。非常有爱的采访。
~
共產黨對高齡黨員都是有關懷的 逢年過節都會去拜訪的 送個米麵油 看看家裡有沒有困難 困難老百姓也會拜訪的 是尊重
我覺得,我是能說服人的。為什麼呢?因為你的心跟我的心並沒有兩樣。能讓我熱淚盈眶的,也許也能讓你起惆悵。
重點是,我根本沒有任何意圖想說服任何人。恰恰因為這樣,你也許反而能見我所見,信我所信。
但我的說服方式比較慢,而且只能是私密家教班。套句維根斯坦對於自己著作的評價,這項說服工作只能一對一進行,就像談戀愛一樣,只能一個對一個訴說情懷,沒法一個對比方說18個。
至於慢,那是性質使然。今天如果我只是要告訴你某個事實,那很快就能辦到。可是,今天如果我是要告訴你一個世界,一種眼光,那就快不起來了。但是,就如梭羅所說,我沒法說服這一代人,但我也許有可能說服你的孫子。
重點是,我根本沒有任何意圖想說服任何人。恰恰因為這樣,你也許反而能見我所見,信我所信。
但我的說服方式比較慢,而且只能是私密家教班。套句維根斯坦對於自己著作的評價,這項說服工作只能一對一進行,就像談戀愛一樣,只能一個對一個訴說情懷,沒法一個對比方說18個。
至於慢,那是性質使然。今天如果我只是要告訴你某個事實,那很快就能辦到。可是,今天如果我是要告訴你一個世界,一種眼光,那就快不起來了。但是,就如梭羅所說,我沒法說服這一代人,但我也許有可能說服你的孫子。
Hölderlin詩兩首。如下。
他的詩,他的憂愁,他的痛苦,他絕望的孤獨,我全都感同身受。
陳真
2025.08.23.
============
《人,詩意地棲居》
譯者不詳
如果人生純屬辛勞,
人就會仰天而問:
難道我所求太多以至無法生存?
是的。只要良善和純真尚與人心相伴,
他就會欣喜地拿神性來度測自己。
神莫測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寧願相信後者。這是人的尺規。
人充滿勞績,
但還詩意地安居於這塊大地之上。
我真想證明,就連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純潔。
人被稱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規?
絕無。
=========
《故鄉》
譯 石 厲
正如船夫帶著他的收穫
從遙遠的島嶼
快樂地返回恬靜的河邊;
我會回到故鄉的
假如我所收穫的多如我所失落的。
從前哺育我成長的可親河岸,
你難道能醫好愛情帶給我的煩惱?
曾經在其中玩耍過的樹林,
如果我回來,還能再一次讓我平靜?
在那清涼的小溪邊,我曾注視著泛起的水波,
河岸旁,我曾望著漂向遠方的小船......
不久我又要回來了,又要見到那些曾經與我相守的山峰,還有故鄉
讓人安全的、也是讓人崇敬的輪廓,
就在母親的屋子裡,我和兄弟姐妹親熱地擁抱,
我將和你們交談,你們纏緊我吧,
像繩索一樣纏緊我,治好我的心病。
親情如故!可是我知道,
愛情帶來的創傷不會很快痊癒,
就是媽媽唱給我的搖籃曲,雖然一直安慰著我,
卻也不能將煩惱從我的胸中驅走。
因為諸神從上天賜給我們火種的時候,
同時也賜給我們痛苦,
因此痛苦永存。我是大地的兒子,我擁有愛,同時我也擁有痛苦。
他的詩,他的憂愁,他的痛苦,他絕望的孤獨,我全都感同身受。
陳真
2025.08.23.
============
《人,詩意地棲居》
譯者不詳
如果人生純屬辛勞,
人就會仰天而問:
難道我所求太多以至無法生存?
是的。只要良善和純真尚與人心相伴,
他就會欣喜地拿神性來度測自己。
神莫測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寧願相信後者。這是人的尺規。
人充滿勞績,
但還詩意地安居於這塊大地之上。
我真想證明,就連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純潔。
人被稱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規?
絕無。
=========
《故鄉》
譯 石 厲
正如船夫帶著他的收穫
從遙遠的島嶼
快樂地返回恬靜的河邊;
我會回到故鄉的
假如我所收穫的多如我所失落的。
從前哺育我成長的可親河岸,
你難道能醫好愛情帶給我的煩惱?
曾經在其中玩耍過的樹林,
如果我回來,還能再一次讓我平靜?
在那清涼的小溪邊,我曾注視著泛起的水波,
河岸旁,我曾望著漂向遠方的小船......
不久我又要回來了,又要見到那些曾經與我相守的山峰,還有故鄉
讓人安全的、也是讓人崇敬的輪廓,
就在母親的屋子裡,我和兄弟姐妹親熱地擁抱,
我將和你們交談,你們纏緊我吧,
像繩索一樣纏緊我,治好我的心病。
親情如故!可是我知道,
愛情帶來的創傷不會很快痊癒,
就是媽媽唱給我的搖籃曲,雖然一直安慰著我,
卻也不能將煩惱從我的胸中驅走。
因為諸神從上天賜給我們火種的時候,
同時也賜給我們痛苦,
因此痛苦永存。我是大地的兒子,我擁有愛,同時我也擁有痛苦。
告兩岸同胞書(10):館長回家的路
陳真
2025.08.22.
館長在深圳據說看了一場動人心弦的無人機表演,末尾數千機群在燦爛夜空打出"回家" 二字。
我也常講回家,光是以 "回家的路" 為題寫的文章恐怕就上百篇。
我們(至少是我)之所以一直想回家,不外就是我離家太久,想家了。我得找到一條回家的路,否則我活不下去。
我對存在主義始終有一種親近性。我喜歡的哲學家或作家例如齊克果、尼采、Karl Kraus、杜斯妥也夫斯基及海德格等等,幾乎清一色是所謂存在主義者。
我甚至把維根斯坦從分析哲學家讀成一個存在主義者。維根斯坦如果能從墳墓裡復活,他將親口證實我對他的理解才是對的。
這其實一點也不難,因為我跟他氣味相投,同類總是能輕易找到同類。你看,維根斯坦最推崇的哲學家也是齊克果,最喜歡的作家是托爾斯泰,最喜歡的詩人是Hölderlin以及早期的R.M.Rilke。這些人我也都喜歡。
維根斯坦最不喜歡的哲學家則是分析哲學家們。維根斯坦說,分析哲學家就是一群拼命剝洋蔥想找出真正洋蔥的笨蛋。
我不是說維根斯坦會從墳墓裡跳出來說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事實上,所有存在主義者都會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因為存在主義者厭惡所有標籤,包括存在主義這個標籤。
存在主義的核心意義其實就一個字:authenticity,講白了就是血肉。
好人也好,壞人也罷,我喜歡有血有肉的人,不喜蒼白,厭惡空洞,尤其痛恨道德教條,討厭低能與造作。每次看到那些空洞低能的什麼論述,我就渾身難受,實在受不了。
一個人講得對錯,做得好壞,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還是得看你這個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跟血肉最不相容的就是虛榮。維根斯坦把自己的思想之根本價值,僅僅建立在一個判準上,那就是他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去除了虛榮。
在我念初中的七零年代,存在主義在全世界盛行,在島內尤其變成愛慕虛榮的進步青年的一種裝飾品,書局裡頭一大堆存在主義的書,讓人(至少是讓我)很反感。厭惡流行、鄙視烏合之眾的存在主義,反倒成為最熱門的流行,成為烏合之眾最炫的裝飾品。
十幾年後,存在主義在島內退了流行,如今已乏人問津,太不炫了。現在是AI人人朗朗上口的年代。
但我覺得,在科技引領一切發展的新時代裡,也許我們需要一點舊思維,也許才能找到一條真正意義上回家的路。
我在祖國大陸各地總是能獲得一種很深很深的安慰與滿足,就好像 "亞利桑那夢遊" 裡頭那隻從水族箱逃往大海的魚一樣。引領前路、吸引我的並不是什麼AI,當然也不是無人機或各種超酷炫科技與建設,而是瀰漫在泥土裡與空氣中、深藏在我血液裡彷彿前世今生的一種家的感覺。
陳真
2025.08.22.
館長在深圳據說看了一場動人心弦的無人機表演,末尾數千機群在燦爛夜空打出"回家" 二字。
我也常講回家,光是以 "回家的路" 為題寫的文章恐怕就上百篇。
我們(至少是我)之所以一直想回家,不外就是我離家太久,想家了。我得找到一條回家的路,否則我活不下去。
我對存在主義始終有一種親近性。我喜歡的哲學家或作家例如齊克果、尼采、Karl Kraus、杜斯妥也夫斯基及海德格等等,幾乎清一色是所謂存在主義者。
我甚至把維根斯坦從分析哲學家讀成一個存在主義者。維根斯坦如果能從墳墓裡復活,他將親口證實我對他的理解才是對的。
這其實一點也不難,因為我跟他氣味相投,同類總是能輕易找到同類。你看,維根斯坦最推崇的哲學家也是齊克果,最喜歡的作家是托爾斯泰,最喜歡的詩人是Hölderlin以及早期的R.M.Rilke。這些人我也都喜歡。
維根斯坦最不喜歡的哲學家則是分析哲學家們。維根斯坦說,分析哲學家就是一群拼命剝洋蔥想找出真正洋蔥的笨蛋。
我不是說維根斯坦會從墳墓裡跳出來說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事實上,所有存在主義者都會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因為存在主義者厭惡所有標籤,包括存在主義這個標籤。
存在主義的核心意義其實就一個字:authenticity,講白了就是血肉。
好人也好,壞人也罷,我喜歡有血有肉的人,不喜蒼白,厭惡空洞,尤其痛恨道德教條,討厭低能與造作。每次看到那些空洞低能的什麼論述,我就渾身難受,實在受不了。
一個人講得對錯,做得好壞,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還是得看你這個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跟血肉最不相容的就是虛榮。維根斯坦把自己的思想之根本價值,僅僅建立在一個判準上,那就是他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去除了虛榮。
在我念初中的七零年代,存在主義在全世界盛行,在島內尤其變成愛慕虛榮的進步青年的一種裝飾品,書局裡頭一大堆存在主義的書,讓人(至少是讓我)很反感。厭惡流行、鄙視烏合之眾的存在主義,反倒成為最熱門的流行,成為烏合之眾最炫的裝飾品。
十幾年後,存在主義在島內退了流行,如今已乏人問津,太不炫了。現在是AI人人朗朗上口的年代。
但我覺得,在科技引領一切發展的新時代裡,也許我們需要一點舊思維,也許才能找到一條真正意義上回家的路。
我在祖國大陸各地總是能獲得一種很深很深的安慰與滿足,就好像 "亞利桑那夢遊" 裡頭那隻從水族箱逃往大海的魚一樣。引領前路、吸引我的並不是什麼AI,當然也不是無人機或各種超酷炫科技與建設,而是瀰漫在泥土裡與空氣中、深藏在我血液裡彷彿前世今生的一種家的感覺。
告台灣同胞書(130):致敬館長
陳真
2025.08.22.
我不太誇人,因為值得誇讚的人真的很少。館長是其一。
雖然我也常會看錯人,但多少還是比一般人會看人。館長四肢發達,但是頭腦並不簡單。懂得看大又看小、鉅細兼顧的人往往絕頂聰明。
除了聰慧,更重要的還是品格與勇氣。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危險處境,不可能不知道私利之所在,但他依然選擇了公義,選擇了真理與真相。
今天,如果台海發生衝突,美國依照慣例,會開出一張死亡清單,往往數千人,下令殺害。
同時也會開出一張保護名單,不外就是一些高價值的人渣走狗,保護其安全,繼續為惡。
我大約能想像島內哪些人會在這兩份名單上。館長毫無疑問會被列為清除對象。一般人只要想到這一點,大概就不敢太明目張膽了。
人類有各種美德,但是勇氣是其他美德的前提。沒有勇氣,其他所謂美德,只是空談。
維根斯坦說,勇氣是擁有不凡思想的門票。意思其實差不多。一個人的言行價值不在於表面上的大小,而在於他為他的言行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館長若能堅持下去,值得我們脫帽致敬。
陳真
2025.08.22.
我不太誇人,因為值得誇讚的人真的很少。館長是其一。
雖然我也常會看錯人,但多少還是比一般人會看人。館長四肢發達,但是頭腦並不簡單。懂得看大又看小、鉅細兼顧的人往往絕頂聰明。
除了聰慧,更重要的還是品格與勇氣。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危險處境,不可能不知道私利之所在,但他依然選擇了公義,選擇了真理與真相。
今天,如果台海發生衝突,美國依照慣例,會開出一張死亡清單,往往數千人,下令殺害。
同時也會開出一張保護名單,不外就是一些高價值的人渣走狗,保護其安全,繼續為惡。
我大約能想像島內哪些人會在這兩份名單上。館長毫無疑問會被列為清除對象。一般人只要想到這一點,大概就不敢太明目張膽了。
人類有各種美德,但是勇氣是其他美德的前提。沒有勇氣,其他所謂美德,只是空談。
維根斯坦說,勇氣是擁有不凡思想的門票。意思其實差不多。一個人的言行價值不在於表面上的大小,而在於他為他的言行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館長若能堅持下去,值得我們脫帽致敬。
館長的覺悟,大格局,非常感動。
摘兩句
好不容易我把橋鑿穿一個洞,現在為了我自己,然後讓它們有議題有時間,再重新再把這個洞補起來。那太虧了。這是2600百萬人的利益,也是14億老百姓的利益,這個利益有多大,不可估算,價值有多高,說多高就有多高,難道我說錯了嗎?
我賣個貨,一件賺個幾塊錢,這什麼東西呀,算了吧,有時候必須放下,你才可以得到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g-Yhw828
想買館長的月餅,缺貨中
摘兩句
好不容易我把橋鑿穿一個洞,現在為了我自己,然後讓它們有議題有時間,再重新再把這個洞補起來。那太虧了。這是2600百萬人的利益,也是14億老百姓的利益,這個利益有多大,不可估算,價值有多高,說多高就有多高,難道我說錯了嗎?
我賣個貨,一件賺個幾塊錢,這什麼東西呀,算了吧,有時候必須放下,你才可以得到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g-Yhw828
想買館長的月餅,缺貨中
紀念翔宇
陳真
2025.08.22.
絕大多數人其實都一般般,不好也不壞。但有極少數人卻令人驚艷,翔宇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醫院的社工同事。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就注意到他的不凡。個子小小的,卻給我一種剛毅正直、心思細膩善良的感覺,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
他過世之前,我在診間花了很長的時間和他討論一個非常棘手的的病患,約好隔天協助病患進行下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步驟。
我當時心裏想:這世界還是有著不平凡的人。他們也許做著很平凡的工作,但他們的正直與善良卻使其言行與氣質顯得如此不凡。
我告訴太太小孩說,我的這個同事像個小巨人,內向寡言,不卑不亢,沒有多餘的情緒與廉價語言,但我能強烈感受到他的正直以及他對人的愛。
沒想到他就這樣突然走了,給了我一個重重的打擊。他的善良與正直,我一生不忘。
=========
獨家/醫院小暖男遭輾斃…同事心碎「才剛圓夢」社工、護理路中斷
TVBS新聞
李東陞 李讚盛
2025年8月20日
莊姓社工平時工作認真,一生奉獻社福,原報考護理系剛收錄取通知,沒想到遇上死劫。(圖/民眾提供)
這位31歲的莊姓社工平日習慣騎著機車長途通勤上下班,同事透露,原本打算做點心給莊姓社工吃,還曾透過通訊軟體告知對方點心製作失敗的消息,但訊息一直未獲已讀,直到隔天早上才得知噩耗。而莊姓社工的社群軟體最後上線時間停留在19日。
同事們回憶,莊姓社工在醫院各部門都相處融洽,是大家眼中的「小暖男」。他工作態度非常認真,奉行「今日事今日畢」的原則。同事表示,莊姓社工其實是個偏內向的人,需要熟悉後才會展現活潑的一面,但因為工作需要,他很努力讓自己變得外向。
讓同事們更加不捨的是,莊姓社工在事發當天下班前才收到護理系的錄取通知簡訊。同事提到,他一直有在準備9月要去就讀護理系的事情,沒想到才剛收到這個好消息,下班後就發生了意外。
據了解,莊姓社工雖然是社工系畢業,但因熱愛護理領域,決定報考護理系,同時也考取了EMT1證照。這次突如其來的噩耗,讓醫院的所有同事都感到非常悲痛與不捨。
陳真
2025.08.22.
絕大多數人其實都一般般,不好也不壞。但有極少數人卻令人驚艷,翔宇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醫院的社工同事。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就注意到他的不凡。個子小小的,卻給我一種剛毅正直、心思細膩善良的感覺,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
他過世之前,我在診間花了很長的時間和他討論一個非常棘手的的病患,約好隔天協助病患進行下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步驟。
我當時心裏想:這世界還是有著不平凡的人。他們也許做著很平凡的工作,但他們的正直與善良卻使其言行與氣質顯得如此不凡。
我告訴太太小孩說,我的這個同事像個小巨人,內向寡言,不卑不亢,沒有多餘的情緒與廉價語言,但我能強烈感受到他的正直以及他對人的愛。
沒想到他就這樣突然走了,給了我一個重重的打擊。他的善良與正直,我一生不忘。
=========
獨家/醫院小暖男遭輾斃…同事心碎「才剛圓夢」社工、護理路中斷
TVBS新聞
李東陞 李讚盛
2025年8月20日
莊姓社工平時工作認真,一生奉獻社福,原報考護理系剛收錄取通知,沒想到遇上死劫。(圖/民眾提供)
這位31歲的莊姓社工平日習慣騎著機車長途通勤上下班,同事透露,原本打算做點心給莊姓社工吃,還曾透過通訊軟體告知對方點心製作失敗的消息,但訊息一直未獲已讀,直到隔天早上才得知噩耗。而莊姓社工的社群軟體最後上線時間停留在19日。
同事們回憶,莊姓社工在醫院各部門都相處融洽,是大家眼中的「小暖男」。他工作態度非常認真,奉行「今日事今日畢」的原則。同事表示,莊姓社工其實是個偏內向的人,需要熟悉後才會展現活潑的一面,但因為工作需要,他很努力讓自己變得外向。
讓同事們更加不捨的是,莊姓社工在事發當天下班前才收到護理系的錄取通知簡訊。同事提到,他一直有在準備9月要去就讀護理系的事情,沒想到才剛收到這個好消息,下班後就發生了意外。
據了解,莊姓社工雖然是社工系畢業,但因熱愛護理領域,決定報考護理系,同時也考取了EMT1證照。這次突如其來的噩耗,讓醫院的所有同事都感到非常悲痛與不捨。
(續)
我認為是態度問題,不是情緒。面對同事或主管,情緒好得不得了,怎麼轉頭面對病人就馬上變臉,兇狠不屑不耐煩,態度非常惡劣。
我認為是態度問題,不是情緒。面對同事或主管,情緒好得不得了,怎麼轉頭面對病人就馬上變臉,兇狠不屑不耐煩,態度非常惡劣。
給院內人員的一封信
陳真
2025.08.18.
成立這群組只有一個目的:拜託善待病人,別再對病人大吼大叫或傲慢無禮了。
我再忍下去,恐怕會爆炸。
來這醫院已經第九個年頭,最大的痛苦就是實在很難忍耐看到醫護或行政人員經常以一種非常惡劣、傲慢以及非常不耐煩、非常厭惡的態度對待病人,離譜程度實在難以置信。
比方說,病人非常非常輕輕地敲門,敲三下,這樣居然也能讓妳暴怒,怒斥病人說只能敲一下。可是,敲門敲一下像在敲門嗎?敲三下到底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而必須遭到兇狠怒斥!我敲門都喜歡敲五、六下不行嗎?
我不敢要求別人視病如親,但是至少不要視病如仇吧!正常地、好好地對待病人有那麼難嗎?
林園地區很多老人,身心各項能力與聽力及行動較為退化不便,我們更應善待他們不是嗎?
病人任何問題來求助或詢問,我們都應該盡最大努力去幫忙都來不及了,怎麼反而還動輒怒斥或不理不睬甚至直接驅逐?
尤其是我這一科的病人特別可悲,他們身心與精神出了問題,我們更應該盡最大努力去幫助他們,回應他們的困難、求救與疑惑都來不及了,怎麼反而還對他們更加不屑更加傲慢無禮。
如果我們看到醫院主管都知道要有禮貌,要打招呼,要趕緊回應主管的要求,趕緊把事情做好,那麼,對待病人難道不是更應該如此嗎?這不是什麼偉大美德,這只是身為醫護人員甚至身為一個人面對長者的本份不是嗎?
醫院不是監獄,病人不是犯人,更不是仇人,妳不用溫柔體貼,也不用赴湯蹈火,只需要溫和對待、盡力協助就行。
我不喜歡當面給人難堪,但我已經當面指正過很多次,不要用那麼惡劣無禮的態度教訓病人,彷彿他們不是一群病患,而是一群關在監獄的歹徒,需要用兇暴怒吼的態度訓話。
輕輕地、溫和地講話有那麼難嗎?
病人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為什麼要如此傲慢兇狠地對待病人?為什麼要喝斥或無端否決病人的求助與疑惑?為什麼總是要對病人大吼教訓?
我不介意大家去喝斥或怒吼醫院主管(如果妳敢的話),但是拜託請對病人好一點,正常一點。不需要溫柔體貼,我只求不要吼叫訓斥,只求切實回應病人的需求或疑問。
我待過、聽過、看過國內外許多醫院,沒看過這麼兇狠的醫院。
管控一下自己的情緒有那麼難嗎?事實上,精神科病人肯定都還比我們更理性更有禮貌情緒更穩定。
希望護理部或其他單位都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九年來,這些問題其實我跟院方講過幾次,但是大多是不同單位,整體情況依然沒有改善。
這其實不是某個人的問題,也不是某個單位的問題,而是一整個院內文化使然。因此,如果把箭頭指向特定個人,其實是不對的。它並不是某個人的問題,而是一整個機構文化缺乏對待病人應有的熱情、專業與尊重。
其他還有許多問題,我再找時間慢慢講。先說一例,比方說,精神科醫師不是白痴,其他科基本的疾病都能處理,毫無困難。而且,我往往都已經開好藥了,妳卻叫病人以後改掛內科。
精神科不就是內科嗎?難道是外科?跟診人員不應該以為自己比醫生更懂,進而在我看診時突然插嘴亂給建議。
這封信,如果要轉傳到全院或其他人員的群組,我也很樂意,我實在是已經忍耐到極限。總之,不要對病人這麼兇這麼冷漠可以嗎?
陳真
2025.08.18.
成立這群組只有一個目的:拜託善待病人,別再對病人大吼大叫或傲慢無禮了。
我再忍下去,恐怕會爆炸。
來這醫院已經第九個年頭,最大的痛苦就是實在很難忍耐看到醫護或行政人員經常以一種非常惡劣、傲慢以及非常不耐煩、非常厭惡的態度對待病人,離譜程度實在難以置信。
比方說,病人非常非常輕輕地敲門,敲三下,這樣居然也能讓妳暴怒,怒斥病人說只能敲一下。可是,敲門敲一下像在敲門嗎?敲三下到底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而必須遭到兇狠怒斥!我敲門都喜歡敲五、六下不行嗎?
我不敢要求別人視病如親,但是至少不要視病如仇吧!正常地、好好地對待病人有那麼難嗎?
林園地區很多老人,身心各項能力與聽力及行動較為退化不便,我們更應善待他們不是嗎?
病人任何問題來求助或詢問,我們都應該盡最大努力去幫忙都來不及了,怎麼反而還動輒怒斥或不理不睬甚至直接驅逐?
尤其是我這一科的病人特別可悲,他們身心與精神出了問題,我們更應該盡最大努力去幫助他們,回應他們的困難、求救與疑惑都來不及了,怎麼反而還對他們更加不屑更加傲慢無禮。
如果我們看到醫院主管都知道要有禮貌,要打招呼,要趕緊回應主管的要求,趕緊把事情做好,那麼,對待病人難道不是更應該如此嗎?這不是什麼偉大美德,這只是身為醫護人員甚至身為一個人面對長者的本份不是嗎?
醫院不是監獄,病人不是犯人,更不是仇人,妳不用溫柔體貼,也不用赴湯蹈火,只需要溫和對待、盡力協助就行。
我不喜歡當面給人難堪,但我已經當面指正過很多次,不要用那麼惡劣無禮的態度教訓病人,彷彿他們不是一群病患,而是一群關在監獄的歹徒,需要用兇暴怒吼的態度訓話。
輕輕地、溫和地講話有那麼難嗎?
病人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為什麼要如此傲慢兇狠地對待病人?為什麼要喝斥或無端否決病人的求助與疑惑?為什麼總是要對病人大吼教訓?
我不介意大家去喝斥或怒吼醫院主管(如果妳敢的話),但是拜託請對病人好一點,正常一點。不需要溫柔體貼,我只求不要吼叫訓斥,只求切實回應病人的需求或疑問。
我待過、聽過、看過國內外許多醫院,沒看過這麼兇狠的醫院。
管控一下自己的情緒有那麼難嗎?事實上,精神科病人肯定都還比我們更理性更有禮貌情緒更穩定。
希望護理部或其他單位都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九年來,這些問題其實我跟院方講過幾次,但是大多是不同單位,整體情況依然沒有改善。
這其實不是某個人的問題,也不是某個單位的問題,而是一整個院內文化使然。因此,如果把箭頭指向特定個人,其實是不對的。它並不是某個人的問題,而是一整個機構文化缺乏對待病人應有的熱情、專業與尊重。
其他還有許多問題,我再找時間慢慢講。先說一例,比方說,精神科醫師不是白痴,其他科基本的疾病都能處理,毫無困難。而且,我往往都已經開好藥了,妳卻叫病人以後改掛內科。
精神科不就是內科嗎?難道是外科?跟診人員不應該以為自己比醫生更懂,進而在我看診時突然插嘴亂給建議。
這封信,如果要轉傳到全院或其他人員的群組,我也很樂意,我實在是已經忍耐到極限。總之,不要對病人這麼兇這麼冷漠可以嗎?
以色列比納粹還邪惡!!人渣黨這些畜生卻用我們的血汗錢去資助以色列。我希望這些魔鬼能遭到報應!!!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v/1LTuyLvapV/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v/1LTuyLvapV/
告台灣同胞書(129):小野大人真機靈
陳真
2025.08.19.
筆名小野的這混蛋,實在是無恥到爆。這一類人,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永遠都是當朝走狗。過去忠黨愛國,口口聲聲中國人,現在卻又是這麼一副嘴臉。
柏楊常說現實比小說還戲劇化。確實如此。
小可愛最近深受周星馳啟發,自己也想嘗試編劇,一直要我幫忙想點子。也許我該跟她說,妳只要多多觀察生活四周,就會發現一些活生生的角色。
比方說,如果你要形塑一個類似像精武門裡頭魏平澳那樣的角色,那妳就觀察小野就是了,看他的神情,看他怎麼講鳥話那副嘴臉,妳也許就知道怎麼創造一個角色了。
不過話說回來,過於戲劇性的角色性格也許不是一種好的創作,因為一般人多少有點廉恥心,不會如此機靈,不會變臉變得這麼迅速而自然。
這樣的角色塑造,也許比較適合拍成喜劇,然而現實卻總是醜陋無比。
=========
舔共藝人要被裁處了!20人名單全曝光 李遠:「正在逐一約談」依法處理
三立新聞網
2025年8月17日
近期,不少台灣藝人赴中國發展期間,曾轉發中共官媒「台灣必歸」貼文,甚至附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稱「中國台灣省」的言論,引發台灣社會關注。陸委會與文化部已展開兩波行政調查,目前已通知20名藝人說明,其中10多人回覆,預計近期將完成裁處。
陸委會發言人梁文傑先前表示,已陸續通知20名藝人,包括歐陽娜娜、侯佩岑、趙又廷、陳喬恩、陳妍希、汪東城等人,若在期限內未回覆,將視同不回應並依法裁處。此舉顯示,台灣政府對藝人涉及統戰或配合中共宣傳的態度,將依法追究,以維護國家主權。
陳真
2025.08.19.
筆名小野的這混蛋,實在是無恥到爆。這一類人,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永遠都是當朝走狗。過去忠黨愛國,口口聲聲中國人,現在卻又是這麼一副嘴臉。
柏楊常說現實比小說還戲劇化。確實如此。
小可愛最近深受周星馳啟發,自己也想嘗試編劇,一直要我幫忙想點子。也許我該跟她說,妳只要多多觀察生活四周,就會發現一些活生生的角色。
比方說,如果你要形塑一個類似像精武門裡頭魏平澳那樣的角色,那妳就觀察小野就是了,看他的神情,看他怎麼講鳥話那副嘴臉,妳也許就知道怎麼創造一個角色了。
不過話說回來,過於戲劇性的角色性格也許不是一種好的創作,因為一般人多少有點廉恥心,不會如此機靈,不會變臉變得這麼迅速而自然。
這樣的角色塑造,也許比較適合拍成喜劇,然而現實卻總是醜陋無比。
=========
舔共藝人要被裁處了!20人名單全曝光 李遠:「正在逐一約談」依法處理
三立新聞網
2025年8月17日
近期,不少台灣藝人赴中國發展期間,曾轉發中共官媒「台灣必歸」貼文,甚至附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稱「中國台灣省」的言論,引發台灣社會關注。陸委會與文化部已展開兩波行政調查,目前已通知20名藝人說明,其中10多人回覆,預計近期將完成裁處。
陸委會發言人梁文傑先前表示,已陸續通知20名藝人,包括歐陽娜娜、侯佩岑、趙又廷、陳喬恩、陳妍希、汪東城等人,若在期限內未回覆,將視同不回應並依法裁處。此舉顯示,台灣政府對藝人涉及統戰或配合中共宣傳的態度,將依法追究,以維護國家主權。
我對鄭麗文刮目相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a64OZTUgo
館長大聲說祖國,我們都是中國人,兩岸聯手天下第一,說出很多人被壓抑以久的心聲,影響逐漸顯現。
補充黃光芹逼黃國昌表態館長的中國人說剪輯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LYjuUrm28
(黃光芹專訪黃國昌的完整影片,可能被下架,找不到)
另外,看完 NOBODY,本質還是爽片,詩人拍得爽片。男主角是絕命律師、絕命毒師裡的律師,我喜歡他的聲音。
我越來越沉默,接電話是恐懼的,我在另一個世界。
以前我不是詩人
看不懂盧梭的《懺悔錄》
但愛極蕭紅的《呼蘭河傳》
她是天生的詩人
早上,事業有成書讀得多很有錢學長橋友
來電推薦
《NOBODY》無名弒
詩人有兩種天分——
一種是美
這部電影很美
開頭五分鐘,我就知道
一種是壞
最好是天生的壞人
關於壞人
我特意寫了首詩
能說的,就這些
因為我是壞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a64OZTUgo
館長大聲說祖國,我們都是中國人,兩岸聯手天下第一,說出很多人被壓抑以久的心聲,影響逐漸顯現。
補充黃光芹逼黃國昌表態館長的中國人說剪輯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LYjuUrm28
(黃光芹專訪黃國昌的完整影片,可能被下架,找不到)
另外,看完 NOBODY,本質還是爽片,詩人拍得爽片。男主角是絕命律師、絕命毒師裡的律師,我喜歡他的聲音。
我越來越沉默,接電話是恐懼的,我在另一個世界。
以前我不是詩人
看不懂盧梭的《懺悔錄》
但愛極蕭紅的《呼蘭河傳》
她是天生的詩人
早上,事業有成書讀得多很有錢學長橋友
來電推薦
《NOBODY》無名弒
詩人有兩種天分——
一種是美
這部電影很美
開頭五分鐘,我就知道
一種是壞
最好是天生的壞人
關於壞人
我特意寫了首詩
能說的,就這些
因為我是壞人
告兩岸同胞書(9):有溝難通
陳真
2025.08.19.
代溝,或是經驗世界有別的一種溝,都是確實存在而難以跨越的。你能溝通理性,溝通任何事實,但你很難溝通不一樣的世界。
許多時候,看一些人的言行,總讓我感到可笑亦可悲。不想傷感情,所以我也就不點名了。比方說,我看到一些擁核者老是辱罵林義雄。罵無妨,但可別罵得太離譜。
林義雄是我的偶像,但是大概沒有人比我批評他批評得更兇。電視台幾次因此要找我上節目談林義雄,但我一概婉拒。
市面上那些低能的辱罵者,總是把林義雄描述成一個與人渣黨政客無異的貪婪猥瑣小人,那就好像把甘地描述成貪婪猥瑣的小人一樣可笑。這樣的辱罵,其實只是羞辱了自己的沒品與低能,而不是羞辱了林義雄。
大學時代,我書桌牆上常貼著兩張紙,一張是林義雄的書法,寫著 "無私無我,死生如一",另一張是我自己寫的 "我為妳狂"。不是寫給哪個女孩的情書,"妳" 指的是我媽媽。
我自認比一般人勇敢,亦無私心。但是比起林義雄的勇氣和人格修養,我自嘆不如。
林義雄是我見過的人裡頭個性最剛烈正直最無私最具有利他精神最視死如歸的一位。我沒見過真的耶穌,但我在林義雄身上能清楚看見耶穌的形象。
如果你連林義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有過什麼樣的事蹟都不了解,那意味著你對台灣八十年代以前的歷史根本一無所知。
其實,人渣黨對異己的所謂迫害程度如果是1,那麼,蔣家王朝的恐怖與血腥就是1000000000000000....,兩者根本連比都不能比,差太多了。
人渣黨這些小癟三,哪配得上什麼法西斯?人渣黨的所謂迫害,事實上如同兒戲,不痛不癢。
在蔣家年代,偶語棄市,文字成獄,幾乎你的任何一言一行都隨時有可能讓你家破人亡人頭落地。若非如此恐怖血腥,哪來十四萬個政治案件?哪來那麼多人被刑求與黑牢折磨得身心破碎?哪來那麼多人伏屍刑場?
有些事我不方便講,但我敢說,如果你知道林義雄受過什麼樣的恐怖刑求,並且舉家老小被國民黨在光天化日下用亂刀斬殺滅門,如果你知道他在這樣的遭遇下的表現,你就知道他人格的剛烈無私與正直。
蔣家王朝的恐怖血腥恐怕是這一代人永遠無法體會的。透過閱讀,你也許可以知道一些,但無法體會。你不可能體會在當年做為一個異議份子所承受的那種極端的恐怖。
在那個年代,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還能有幾天的自由,幾天的活命。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父母或家人是否會遭你連累而家破人亡。
這年頭,所謂遊行示威就跟健身郊遊沒兩樣,但是我們當年第一次決定要打破戒嚴惟一死刑的禁令,決定走上街頭跟蔣家拼命時,根本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活著回來。當年的兩份遺書,至今我都還留著。
所謂惟一死刑罪,意思就是在戒嚴令底下,三人以上聚眾抗議,就是叛亂。根據戒嚴令,叛亂罪只有惟一一種判決,就是槍斃。
在戒嚴年代,平常在我租的房間裡頭,在床頭與門口處,我總藏著兩把刀,以備不時之需,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明天。這才叫做白色恐怖法西斯。人渣黨算哪根蔥?
人渣黨的壞,不在於他的血腥與殘酷,而是在於他的徹底敗德與無盡的貪婪,毫無任何真實理想,一切都只是隨時可以改變說法的撈錢奪權工具。
但是蔣家不是這樣。蔣氏父子始終是愛國者,他們有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對異己、對批評者非常殘暴血腥,但他們並不想傷害絕大多數人民。然而人渣黨卻是只要有私利可圖,他便可以毫不猶豫地出賣兩千三百萬人的性命與身家財產。說他們是什麼台獨份子,那完完全全不是事實。
將來台灣解放後,我敢保證他們將會比誰都更加 "熱愛" 祖國,"熱愛" 共產黨。事實上是熱愛人民幣,熱愛權位。
我熬過了那段痛苦慘烈的青春歲月,但我連累了父母,我使他們生前蒙羞,飽受折磨。往事已矣,但我知道我心裏的傷永遠無法癒合。
林宅滅門血案後,林義雄大女兒林奐均身中六刀,是唯一生還者。林義雄後來去美國念書,有一次帶奐均去湖邊玩,奐均玩得很開心,但是林義雄說他覺得自己好像喪失了快樂的能力。
從1991年我媽媽因我而過世至今,我也常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有什麼東西從我心裡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
陳真
2025.08.19.
代溝,或是經驗世界有別的一種溝,都是確實存在而難以跨越的。你能溝通理性,溝通任何事實,但你很難溝通不一樣的世界。
許多時候,看一些人的言行,總讓我感到可笑亦可悲。不想傷感情,所以我也就不點名了。比方說,我看到一些擁核者老是辱罵林義雄。罵無妨,但可別罵得太離譜。
林義雄是我的偶像,但是大概沒有人比我批評他批評得更兇。電視台幾次因此要找我上節目談林義雄,但我一概婉拒。
市面上那些低能的辱罵者,總是把林義雄描述成一個與人渣黨政客無異的貪婪猥瑣小人,那就好像把甘地描述成貪婪猥瑣的小人一樣可笑。這樣的辱罵,其實只是羞辱了自己的沒品與低能,而不是羞辱了林義雄。
大學時代,我書桌牆上常貼著兩張紙,一張是林義雄的書法,寫著 "無私無我,死生如一",另一張是我自己寫的 "我為妳狂"。不是寫給哪個女孩的情書,"妳" 指的是我媽媽。
我自認比一般人勇敢,亦無私心。但是比起林義雄的勇氣和人格修養,我自嘆不如。
林義雄是我見過的人裡頭個性最剛烈正直最無私最具有利他精神最視死如歸的一位。我沒見過真的耶穌,但我在林義雄身上能清楚看見耶穌的形象。
如果你連林義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有過什麼樣的事蹟都不了解,那意味著你對台灣八十年代以前的歷史根本一無所知。
其實,人渣黨對異己的所謂迫害程度如果是1,那麼,蔣家王朝的恐怖與血腥就是1000000000000000....,兩者根本連比都不能比,差太多了。
人渣黨這些小癟三,哪配得上什麼法西斯?人渣黨的所謂迫害,事實上如同兒戲,不痛不癢。
在蔣家年代,偶語棄市,文字成獄,幾乎你的任何一言一行都隨時有可能讓你家破人亡人頭落地。若非如此恐怖血腥,哪來十四萬個政治案件?哪來那麼多人被刑求與黑牢折磨得身心破碎?哪來那麼多人伏屍刑場?
有些事我不方便講,但我敢說,如果你知道林義雄受過什麼樣的恐怖刑求,並且舉家老小被國民黨在光天化日下用亂刀斬殺滅門,如果你知道他在這樣的遭遇下的表現,你就知道他人格的剛烈無私與正直。
蔣家王朝的恐怖血腥恐怕是這一代人永遠無法體會的。透過閱讀,你也許可以知道一些,但無法體會。你不可能體會在當年做為一個異議份子所承受的那種極端的恐怖。
在那個年代,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還能有幾天的自由,幾天的活命。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父母或家人是否會遭你連累而家破人亡。
這年頭,所謂遊行示威就跟健身郊遊沒兩樣,但是我們當年第一次決定要打破戒嚴惟一死刑的禁令,決定走上街頭跟蔣家拼命時,根本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活著回來。當年的兩份遺書,至今我都還留著。
所謂惟一死刑罪,意思就是在戒嚴令底下,三人以上聚眾抗議,就是叛亂。根據戒嚴令,叛亂罪只有惟一一種判決,就是槍斃。
在戒嚴年代,平常在我租的房間裡頭,在床頭與門口處,我總藏著兩把刀,以備不時之需,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明天。這才叫做白色恐怖法西斯。人渣黨算哪根蔥?
人渣黨的壞,不在於他的血腥與殘酷,而是在於他的徹底敗德與無盡的貪婪,毫無任何真實理想,一切都只是隨時可以改變說法的撈錢奪權工具。
但是蔣家不是這樣。蔣氏父子始終是愛國者,他們有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對異己、對批評者非常殘暴血腥,但他們並不想傷害絕大多數人民。然而人渣黨卻是只要有私利可圖,他便可以毫不猶豫地出賣兩千三百萬人的性命與身家財產。說他們是什麼台獨份子,那完完全全不是事實。
將來台灣解放後,我敢保證他們將會比誰都更加 "熱愛" 祖國,"熱愛" 共產黨。事實上是熱愛人民幣,熱愛權位。
我熬過了那段痛苦慘烈的青春歲月,但我連累了父母,我使他們生前蒙羞,飽受折磨。往事已矣,但我知道我心裏的傷永遠無法癒合。
林宅滅門血案後,林義雄大女兒林奐均身中六刀,是唯一生還者。林義雄後來去美國念書,有一次帶奐均去湖邊玩,奐均玩得很開心,但是林義雄說他覺得自己好像喪失了快樂的能力。
從1991年我媽媽因我而過世至今,我也常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有什麼東西從我心裡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
告兩岸同胞書(8):歡迎大家親自下海試試
陳真
2025 08.19.
以館長將在大陸設公司,來對他進行道德審查甚至道德裁判是毫無道理的,因為:
ㄧ,以館長的影響力來說,如果他肯昧著良心,一如絕大部份所謂菁英及知識份子那樣,他將吃喝不盡。
他甚至不需要像所謂菁英或知識份子那樣無恥下三濫,只需要選擇站在人渣黨與美國那一邊,偶爾喊喊愛台灣,億萬財富與榮華富貴及各種功名利祿將垂手可得。
館長如此,而我自己不也如此?我們還需要去向彼岸謀取名利嗎?
但我們非但沒有昧著良心,也沒有明哲保身接受垂手可得的榮華富貴,而是選擇直接與島內邪惡勢力為敵。
我不是今天才出社會,應該很難被表面言行所騙。事實上,自余束髮以來,即從事革命,如今已四十幾年,除了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如林義雄、陳菊等人之外,島內很難找到幾個比我更資深更深入、貢獻更大的黨外元老了。我知道哪些人是真是假,我知道什麼是演戲,什麼是職業,什麼是真心。
島內很多網紅、名嘴以及幾乎所有政治人物的所謂反綠或親中,其實只是一種職業,一種功名利祿的經營手段,他們罵綠罵得再兇也沒用,依然是戲,罵與被罵的雙方彼此心知肚明。即便他們表面上站在綠營的對立面,我敢保證他們絕不會因此受到一丁點傷害。
事實上,他們與綠營私下全是好朋友,在檯面上演戲給大家看。人渣黨不會跟你計較,因為他們也不是政治白痴,當然知道誰是自己人,知道誰有害誰無害。
柯文哲之所以遭到迫害是因為,綠營及其美國主子發現他逐漸不受控,竟然打算跟對岸談判,玩真的,而這也是為什麼對岸早在他當第一任台北市長時便押寶他的原因。
除此之外,在島內,如果你真的反綠,真的支持中國共產黨,那我敢保證,除非你毫無名氣或影響力,或是除非你匿名,否則,任何一個人只要與人渣黨公然為敵,必然會遭受各種卑鄙下流的政治報復,付出巨大代價。不信的話,歡迎大家親自下海試試。
二,一個人的言行,其內在本質與深度具有某種獨立判準,即便當事人因此獲利,依然不足以因此否定其內在真實與外在價值。
比方說,如果我老誇某家醫院是全世界最好的醫院,哪天我如果成為這家醫院的領導,難道我就因此而顯得道德卑鄙?難道我對這醫院的真實評價就因此而應該被否定?這樣一種理解方式合理嗎?
陳真
2025 08.19.
以館長將在大陸設公司,來對他進行道德審查甚至道德裁判是毫無道理的,因為:
ㄧ,以館長的影響力來說,如果他肯昧著良心,一如絕大部份所謂菁英及知識份子那樣,他將吃喝不盡。
他甚至不需要像所謂菁英或知識份子那樣無恥下三濫,只需要選擇站在人渣黨與美國那一邊,偶爾喊喊愛台灣,億萬財富與榮華富貴及各種功名利祿將垂手可得。
館長如此,而我自己不也如此?我們還需要去向彼岸謀取名利嗎?
但我們非但沒有昧著良心,也沒有明哲保身接受垂手可得的榮華富貴,而是選擇直接與島內邪惡勢力為敵。
我不是今天才出社會,應該很難被表面言行所騙。事實上,自余束髮以來,即從事革命,如今已四十幾年,除了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如林義雄、陳菊等人之外,島內很難找到幾個比我更資深更深入、貢獻更大的黨外元老了。我知道哪些人是真是假,我知道什麼是演戲,什麼是職業,什麼是真心。
島內很多網紅、名嘴以及幾乎所有政治人物的所謂反綠或親中,其實只是一種職業,一種功名利祿的經營手段,他們罵綠罵得再兇也沒用,依然是戲,罵與被罵的雙方彼此心知肚明。即便他們表面上站在綠營的對立面,我敢保證他們絕不會因此受到一丁點傷害。
事實上,他們與綠營私下全是好朋友,在檯面上演戲給大家看。人渣黨不會跟你計較,因為他們也不是政治白痴,當然知道誰是自己人,知道誰有害誰無害。
柯文哲之所以遭到迫害是因為,綠營及其美國主子發現他逐漸不受控,竟然打算跟對岸談判,玩真的,而這也是為什麼對岸早在他當第一任台北市長時便押寶他的原因。
除此之外,在島內,如果你真的反綠,真的支持中國共產黨,那我敢保證,除非你毫無名氣或影響力,或是除非你匿名,否則,任何一個人只要與人渣黨公然為敵,必然會遭受各種卑鄙下流的政治報復,付出巨大代價。不信的話,歡迎大家親自下海試試。
二,一個人的言行,其內在本質與深度具有某種獨立判準,即便當事人因此獲利,依然不足以因此否定其內在真實與外在價值。
比方說,如果我老誇某家醫院是全世界最好的醫院,哪天我如果成為這家醫院的領導,難道我就因此而顯得道德卑鄙?難道我對這醫院的真實評價就因此而應該被否定?這樣一種理解方式合理嗎?
雖說先前的確被館長的話語和一些鏡頭感動,
這幾天也每天都看他深圳行的影片看得入迷,
尤其昨天他拜訪高巨創新(無人機公司),
即便晚上已是大風大雨已不適合無人機飛,
公司的老闆認為館長此行都已來了,
沒能如期升空實在有些不夠暢快,
於是豪氣干雲在風雨中升起了2000架無人機,
在夜晚作了一場簡短卻美麗精彩的展演,
最後無人機排成了一個美麗中文的「家」字,
實在讓人難忘。
不過在投入許多精力時間看館長近期的影片後,
興起我也再找尋了他目前經營的商品和健身房狀況,
查了一些資料後赫然想起為什麼我先前一直對館長有些不信任,
因此我個人對他的看法並沒有板上各位前輩朋友們來得高,又帶回一些保留。
不過此時此刻實在是不適合當掃興烏鴉,
可以確定的是他的影響力的確會讓更多臺灣人去瞭解大陸,至少願意去打開那個念頭,
有機會能鬆動一些長期下來深錮在臺灣的綠濾鏡。
這幾天也每天都看他深圳行的影片看得入迷,
尤其昨天他拜訪高巨創新(無人機公司),
即便晚上已是大風大雨已不適合無人機飛,
公司的老闆認為館長此行都已來了,
沒能如期升空實在有些不夠暢快,
於是豪氣干雲在風雨中升起了2000架無人機,
在夜晚作了一場簡短卻美麗精彩的展演,
最後無人機排成了一個美麗中文的「家」字,
實在讓人難忘。
不過在投入許多精力時間看館長近期的影片後,
興起我也再找尋了他目前經營的商品和健身房狀況,
查了一些資料後赫然想起為什麼我先前一直對館長有些不信任,
因此我個人對他的看法並沒有板上各位前輩朋友們來得高,又帶回一些保留。
不過此時此刻實在是不適合當掃興烏鴉,
可以確定的是他的影響力的確會讓更多臺灣人去瞭解大陸,至少願意去打開那個念頭,
有機會能鬆動一些長期下來深錮在臺灣的綠濾鏡。
以前我不是詩人
看不懂盧梭的《懺悔錄》
但愛極蕭紅的《呼蘭河傳》
她是天生的詩人
早上,事業有成很有錢舊識學長
橋友,推薦
《NOBODY》無名弒
詩人有兩種天分——
一種是美
這部電影很美
開頭五分鐘,我就知道
一種是壞
最好是天生的壞人
關於壞人
我特意寫了首詩
能說的,就這些
看不懂盧梭的《懺悔錄》
但愛極蕭紅的《呼蘭河傳》
她是天生的詩人
早上,事業有成很有錢舊識學長
橋友,推薦
《NOBODY》無名弒
詩人有兩種天分——
一種是美
這部電影很美
開頭五分鐘,我就知道
一種是壞
最好是天生的壞人
關於壞人
我特意寫了首詩
能說的,就這些
告兩岸同胞書(7):革命的誕生
陳真
2025.08.18.
黃帝內經與本草綱目記載,腦殘是絕症,沒藥醫的,除非醫神再世。
我看館長就是醫神。其他人則是庸醫。
一帖處方是否良藥,得看你的病症而定。我們(至少是我)上網寫這些東西,當然是為了治療腦殘,而不是來參加作文比賽。
科學之難,難不過製造一個科學典範的轉移。文史哲之難,難不過改變信仰。
神醫跟哲學家有一點相似之處就是深入淺出化繁為簡的能力。與此相反則是低能。
我不好意思點名,舉一些名嘴學者專家為例,畢竟他們也不是壞人,沒必要傷感情。
這些庸醫的特色就是很愛論述,論述無妨,但是你把兩三句話就能講清楚的想法,卻亂吊不相干的書袋講得不知所云,豈不是很蠢?
但是,一般讀者卻是這樣,當他看到一堆書袋,不知所云時,他不會覺得作者腦子進水,而是覺得他好棒,好有內涵,是自己程度太差所以看不懂。
反之,當他看到一個人寫文章,一下幹他媽,一下操他爸,心裡就會覺得作者好沒水準,事實上卻剛好相反。
除了化繁為簡深入淺出之外,神醫還有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直接打要害,打它最為理所當然的核心。
比方說,如果今天我想要攻擊知識本質的絕對性,那我最好的攻擊目標就是數學,而不是攻擊比方說歷史。為什麼呢?因為一旦連數學的知識論地位(epistemological status)都不具備絕對性,那麼,知識這一整座大廈便搖搖欲墜,知識革命就誕生了。
陳真
2025.08.18.
黃帝內經與本草綱目記載,腦殘是絕症,沒藥醫的,除非醫神再世。
我看館長就是醫神。其他人則是庸醫。
一帖處方是否良藥,得看你的病症而定。我們(至少是我)上網寫這些東西,當然是為了治療腦殘,而不是來參加作文比賽。
科學之難,難不過製造一個科學典範的轉移。文史哲之難,難不過改變信仰。
神醫跟哲學家有一點相似之處就是深入淺出化繁為簡的能力。與此相反則是低能。
我不好意思點名,舉一些名嘴學者專家為例,畢竟他們也不是壞人,沒必要傷感情。
這些庸醫的特色就是很愛論述,論述無妨,但是你把兩三句話就能講清楚的想法,卻亂吊不相干的書袋講得不知所云,豈不是很蠢?
但是,一般讀者卻是這樣,當他看到一堆書袋,不知所云時,他不會覺得作者腦子進水,而是覺得他好棒,好有內涵,是自己程度太差所以看不懂。
反之,當他看到一個人寫文章,一下幹他媽,一下操他爸,心裡就會覺得作者好沒水準,事實上卻剛好相反。
除了化繁為簡深入淺出之外,神醫還有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直接打要害,打它最為理所當然的核心。
比方說,如果今天我想要攻擊知識本質的絕對性,那我最好的攻擊目標就是數學,而不是攻擊比方說歷史。為什麼呢?因為一旦連數學的知識論地位(epistemological status)都不具備絕對性,那麼,知識這一整座大廈便搖搖欲墜,知識革命就誕生了。
真的很開心看到聲志的留言,我是他的親妹妹。我最近因為哥哥的原因,接觸了托爾斯泰,因為我是基督徒,所以看“復活”看的津津有味,而且是他晚年的作品,批判性沒有那麼強。至於沈從文,我跟哥哥一樣看不懂;赫塞不止“流浪者之歌”連他“徬徨少年時”也是經典,還有托爾斯泰的“懺悔錄”是自我批判性很強的書,有空閒、有時間可以看看喔!
力民兄,是這樣,館長的水準相當不錯,遠勝藍營傾向統派的名嘴們。藍營名嘴似乎都沒明說自己是統派,且腦子多少仍有藍營鄙視中共的固化思維+藍色史觀+藍色習氣。簡單說是反動派的底色,我跟藍人這樣講,他們莫不氣炸。藍人始終認為大陸近年是因為改過遷善所以才有高度發展,他們不承認也不知道中共本來就比他們先進,也不同意蔣介石發動412之後國民黨就不再具備領導全中國的資格。至於後來國民黨中央撤退來台,兩蔣和國民黨屬中國人政權當然有資格來台,只是以他們的腐敗本質來說不配來台,早該好好投降。
我沒那麼愛罵蔣介石,尤其當我在小紅書看到蔣友青視頻中的可愛(他精神受到很大摧殘過,目前看起來穩定),使我不忍心老罵兩蔣。蔣友青比蔣萬安可敬一百倍。
至於館長和新黨三劍客和邱毅相比,也沒比他們遜色,風格各自不同罷了。這四位頂多只有林明正比他對新中國的歷史知識懂得多,尤其林明正這幾年還花費工夫研究左翼和社會主義(館長也正大量吸收這方面,只是沒那麼學術,他光研究大陸如何扶貧就值得點讚)。還有,林明正的論述能力一直在進步中,我聽過他講演,很能講,甚至比視頻中還棒。我不認識林明正,只是我的觀察如上。
淺一點來說,林明正在微博曾說自己看過大決戰三部曲的電影,館長可能才正要補課。蘇恆、王炳忠、邱毅可能也看過,但可能沒法像林這麼會聊或愛聊這種話題。要懂大陸要花時間,而且不能有成見。譬如大陸網友講林總、林帥、101,指的是林彪。鄧小平代號叫總設計師。毛主席叫教員。館長不必懂這麼細,不然他一天可能只睡一小時。館長最近看到1984年大陸閱兵的畫面而驚嘆,這我早已預料有大陸網友會告訴他,因他很愛看網友留言。不是每個網紅或大V都很愛自己的粉絲,頂多留言看兩眼,架子大,懶得回也罷,更不肯學習。
兩岸閱兵史,我三年前寫過一篇可參考:
https://wczhang.blogspot.com/2022/08/blog-post_28.html
館長目前不足的是無法看到大陸中下層老百姓怎麼生活,他只看大陸尖端發展的一面。如果他能看到前者,他會更讚賞大陸。
我將上個月寫的館長一文重新整理,刪掉幾千字,又新增幾句,總共留下8000字,還是很多字但不得不。在此用簡中貼出。繁體連結則在此:
https://wczhang.blogspot.com/2025/08/blog-post_18.html
以下容我佔用版面多一點,因我要貼簡中之全文。目的是方便大陸網友轉貼,這樣才更理解館長這個人。我私下不認識他,包括本篇前面提到的人名我沒一個私下認識。但我認為我看得出他的成色。電影天下無賊有過一句很好笑,黎叔(葛優)說:「我倒是有興趣,驗驗這對鴛鴦的成色。」指的是劉德華、劉若英。反正很好笑就對了。我不是說我是武林至尊黎叔的意思,只是借用「成色」。
《开弓没有回头箭:馆长陈之汉首次大陆行的转变》
一,馆长的进步性
2025年馆长六月上旬到中旬首次前往大陆,近两个月来堪称震撼台湾,且六次登上央视(截至8月17日为止;本文原稿写于7月28日,此为浓缩版)。
很多台湾人讶异他怎么变得这么会讲。
惊艳的不光是馆长思想转向,而是他很会讲,口才极佳。很多人觉得他以前很废,倒不是他挺过谁,一码归一码,他脑袋和口条很贫乏,所谓论述能力,很菜。又如他的搞笑,对打,譬如跟啥“吃屎哥”,低能到不行。两岸许多网友喜欢他爆粗口,当他是乐子人,或崇拜,大多都是压抑惯了,或生活太过乏味?
馆长是如何顿悟的?他的智慧是如何升级的?这带来一个启示,人人都可以是食神。
简单说,人一旦开窍了,一通百通。粤语叫:「一理通百理明。」
我的观察和研判,他的开窍跟他私下研究大陆,看各种视频,往返两岸的本岛民间人士跟他聊大陆有关。以及可能有高人指点。
很多台湾同胞至今不晓得,大陆视频、文章、影视的素质很高(大陆观众认为很多影视低能或乱拍另当别论),所谓高手在民间,各路专业的人都很多,各种面向十分之灿烂。馆长从中吸收到养分,加上有慧根,整个开窍。
2024年大陆B站的女性博主“吃瓜蒙主”曾说,台湾教育失败,台湾人讲话和写东西不利索,没法清清爽爽,文章无法理得明明白白,台湾人的文化越来越次。顺着蒙主这番话来说,馆长默默吸收了许多大陆视频的灵气,如今脑子和口条理得明明白白,智慧豁然升级。
他在前往大陆前就开窍一半了,去大陆只是印证看法,印证过后自而信心百倍,全然开窍。此人是做生意的,竟然还46岁了没去过大陆。他很想去!想去就学得更多。大陆能学到的、能见识的东西太多了。
一字记之曰:心。
从接触大陆资讯到前往祖国,起初是好奇,尤其是想给绿营难堪,基于恨绿,但这演变成他发现自己被台湾蒙蔽了,所谓台蛙,信息茧房,他发现这事儿得认。认自己过去脑残。
从而他为过去道歉多次,试问蓝绿白政客网红有无对自己歉疚半次过。不是说他道歉多伟大(他也是不得不),但已然不容易了。
他一通百通之后,慨然讲出祖国、中国人、大陆,以及用他简单精准的俗白方式来论述两岸走在一起的重要。包括他想止战,想拉下绿营,想救柯文哲。这些都很打动人呀。
事实上当他首次造访大陆,来到上海落地的第一天,做直播时仍不断中国、中国的讲话。第二天就改成大陆。后来他告诉大家,大陆群众有人告诉他为何要讲大陆,我们对台湾同胞这么友善,听你们老讲中国伤感情。意思就是你们有分别心。可以看出「伤感情」这句让馆长很在意,颇内疚。大陆同胞的真诚,让馆长也变成一个真诚的人,那些表情是演不来的。
这不光是人情世故的假来假去,而是在意伤感情,这种人特别成熟智慧,心肠也好。他伤了别人感情,别人有点受伤,他也跟着受伤,他有这种体会能力,这种人不容易。本人2009年曾前往台大聆听侯孝贤导演一场文艺讲演,他建议台下青年:「要能感受别人的感受。」眼下是十六年后的2025年,读书人普遍有无作到这句值得打个问号,可状似大老粗的馆长却体现了这句。
他的思想和口条表达能力是一起进步的,这种进步才叫扎实,也生出了魂魄。从个人的进步,到民族情感、两岸情感的对接,一瞬间他彻底接通了一切。有点素人禅师的味儿了这是。
二,馆长的人民性
本单元较长,分三小单元。三小并非闽南语粗口,亦可能我来个擦边胡闹。
1、志愿役的傻逼
事实上,有不少台商、台生(尤其去大陆的短期交换生)即使常在、或曾在大陆生活,但对大陆多少带着歧视眼光。他们非常需要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遇到彼此有利益关系或精台的大陆同胞更是烂在一块儿。
可喜的是馆长不是这种人。这跟馆长的阶级背景可能有关。他是祖籍宜兰的台北人,但属底层草根气息。他当兵签下陆战队志愿役。从资料来看是「转服」,即入伍新训后从义务役改签转服志愿役。基本上签下转服志愿役的多半是草根、中产家庭或一般保守家庭长大的。
坦白说这种人在军中常被人背后取笑。只因被认为是没出息的笨蛋,当兵这种鬼日子,国军那么腐败,却签下去。他们一门心思在军中老实存钱,但被很多弟兄私下讥笑是浪费青春,没有进取心,不敢在社会上闯荡。有些志愿役在部队当个士官就骄横,还爱讲当士官背责任多苦。不少底层弟兄在国民中学因不爱念书,辍学后学习了一门手艺就收入不少;譬如学木匠、修水电、做铝门窗等,老年代的收入更多。他们看不上签志愿役的废物(喂),大专兵本身的优越感就不用说了(大专兵烂透在军中是共识),他们也看不上志愿役。
一般来说,在台湾当兵不像大陆人加入解放军的光荣感那么大,取笑转服的人是常态,甚至退伍后在社会上仍被人笑问:「奇怪你当初怎会签下去?」、「军中成天在造假你受得了?」、「你这么爱当兵不如早几年进士校或考官校?」问题是官校入学的成绩不能太差。有的大专兵在新训中心(竟然)自愿转服预官,这也是签下志愿役的一种,背地里遭笑话亦属常态。
在此还得说明一下,以前的志愿役士官是有区分的。如果你是国中毕业去读士校的那种志愿役,在军中好受人尊敬,他们清一色出身寒门,被爸妈叫来读士校,特能吃苦,身上有战技,下部队后本职学能很强,一路当到上士退伍。可如果你是20岁或19岁入伍(一般20岁收到征兵令,馆长自愿申请提早一年当兵),之后在新兵训练中心被军方游说后改签的转服,这种容易被弟兄们看不上,菜的时候还被老兵欺负算正常。这种大概当三年半、23-24岁中士退役,除非你再签下去。本岛部队长年是老鸟爱欺负或霸凌菜鸟,甚至虐出人命,老鸟常说这叫「传统」,或流行骂兵:「你这个死老百姓。」这不是大陆以人民军队做号召的文化能想象的。
谈这些绝不表示看不起人是对的,只是讲解老年代志愿役在军中的生态文化。每个人的生涯规划都必须被尊重,每个人家庭状况不同。
话回馆长,他曾在网络上谈自己在陆战队吃了苦,受了折磨,被整冤枉,似乎没吃到太多志愿役的红利。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台湾很多男人退伍后喜欢谈当兵吃苦、多操、多惨烈,虽难免有欢乐吹牛成份(女人根本懒得听),但如果当事人把吃苦的价值、荣誉放得很高,这种人通常没有辜负他受的罪,是个真男人,他们之后回到社会上都韧性十足。
馆长1979年生,照理说他服役时本岛部队训练变成很轻松了,但海陆属特种兵,仍有一定程度的艰辛「遗绪」传下,多少仍具谈资,他重视军中吃的苦,这值得给他点赞。他就算没当网红,单单能从谷底、憋屈的各种阶段一路摸爬滚打而至奋起创业,完成了开设健身房的人生梦想,在社会上寻得一席之地,这已然值得尊敬。当然这不是说他事业无成的话就该被看低,我自己就一事而成可不是。
在馆长的年幼时期,本来家境挺好,然因父亲早逝,家里有点家道中落,才让他变成类似草根阶级。一般来说,什么阶级就带来什么气息,但有时也不准确,有的人接地气的天赋高、慧根够,自可融合巧妙。李敖是读书人但有少见的草莽性格,有流氓气。馆长不是读书人但讲话比读书人精准有料。民间很多平民百姓或读书人都很爱聊政治,但像馆长能聊出含金量的,坦白说不多。他比「话糙理不糙」的大妈大爷还厉害,而且他其实内容并不糙。甚至他的大块头模样、年轻时的道上色彩、浓郁的草根气息,反而都成了障眼法。就像古早时期唱铜锤花脸的金少山,扮相和声腔是一个粗勇豪迈、大嗓门的人,但心思细腻得很,绝对称得上是艺术家。
举凡(以前我服役时的连长成天爱讲举凡)阶级背景、草根气息、工农兵的味儿、志愿役经历之种种,看来对馆长这人的基调有很大的影响。简单说,这种摸爬滚打、吃过苦的孩纸对人比较能用平常心,平等心去相待,去搏感情。而且馆长可贵的是模样憨厚(或憨傻),这种人重视真心,相信真心,并不会变油。
说到憨厚,固然台商也有很多是草根大老粗、农工兵子弟出身,可前面讲到不少台商对大陆心态不好(我相信台商们都开心馆长来大陆,但这和台商在大陆爱吹牛且多少带点高姿态的德行是两回事),中产小资出身的台商当然大多也蛮糟,但馆长这人并非如此。馆长对大陆的可说动了真情,憨憨的,这是他的独特性,这点蛮珍贵。倒也不能全用阶级来套,譬如有些人家世不错但对大陆的心态很友善,当然这种人在岛内也对各种人不会有成见,不会自以为高尚,总之这种人是极少数。说到底台湾人不分阶级背景学历贫富南部北部,大多就是看不上大陆,很爱用台湾人的身份来靠夭,来讲大陆这个那个的。这种鸟样子是蓝绿统治本岛几十年来造成的。其中文青的嘴脸尤其糟糕。大陆文青也烂,也看不上大陆,自认洋派的作家、导演、公知和文青一大把。还好馆长没接触这种二百五。馆长接触的大陆属「人民群众」居多,气味相投或相近。算他运气好。
2、志仁补校的无敌学历
馆长的履历中最牛的不是志愿役的憋屈,而是,靠杯,他来自台北最接地气的几所「烂」学校之一。他读过协和工商,最后在志仁补校毕业。协和当然很废,志仁更废,说废到最底部不算污辱。开玩笑的,此「废」有生命力之意。协和的女生在我那个年代很正,她们比较不爱念书,只是这样。我记得以前协和的男生少。高中时,我们班上有些被留级的同学,他们跟我挺要好的,他们升不上高三,留级高二,然后撑一年后好几个要转去志仁洗学历,这些好友被爸爸骂干、或揍翻,少不了被骂败家子。可见我这几个同学有多杰出!他们很聪明但就是不想念书,坐不住,爱玩。这些被俗世看不上的学历(根本拿不出手的学历)反而是他们生命力昂扬又靡废的人生资产。
摊开馆长的成长史,他的年纪恰恰接到这些学校充满特色的年代。全省以前还有许多五专、三专、二专,都很接地气。同理,多少也有刻板印象,我表妹(1976年次)是中国工商(五专时期)毕业的,她一直很乖巧且聪慧。
我曾执教过一年高职夜间补校。当时是90年代中期在基隆。补校都是在晚上上课,学生大多白天打工。这批孩子有一半年龄和馆长相仿,他们不爱念书(学习)或因缘际会失去学习机会,白天学手艺或做粗工,晚上来补校是花钱洗学历,希望自己拥有一张高中或高职文凭。男同学大多江湖气重,有的年纪还比我这个老师大。女生倒是不惹事,只是接地气。
我那年当高三补校的班导(班主任),一次同学们上课聊天的声音太吵,我走到一个坐最后一排的男生面前,把他身边没人坐的一把空椅子高高举起,在他面前砸烂,木头椅子粉碎一地。全班鸦雀无声。这男生羞愤,他个儿高,整个人跳起来,飙粗口,叫板「出来讲!」闽南语,意思邀我去走廊打一架。这人平时本就流氓味,一时间对峙起来……
我心想这下完了,缓和自己情绪十来秒钟后,我不卑不亢的跟他诚恳说:「是我冲动了,我跟你道歉。」从而危机化解。此后班上许多男孩子对我更热情,当我是铁哥们。他们几度激动的对我说:「我们长这么大没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过对不起。」其实我一半的原因是怕挨揍,另一半原因是多年来从小本就有错会主动认错,且认了反而轻松,我对真理的兴趣大过面子。这个对我暴粗口的男生后来对我相当义气帮忙。略下。
他们是被社会看不上或歧视的孩子,有人对他们好,他们跟你拿心换心。
所以为何我看得懂馆长觉得他很可以,这是基本的人生阅历。(这两句啰唆了,根本不必我这些生活经验观察接触,我想你也看得懂的。)
3、新中国的活泼松势和细致多情
众所周知,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是以无产阶级立国的,至今(2025)七十六年来虽然历经思想路线斗争动荡和选择,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改成自由经济,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还是在,人民性的气息还是化在每一代人的风格中(大陆文青例外啦干),他们大多作风一派自然流利,潇洒得很,很接地气,不矫情,不装逼。
譬如我在大陆,一个男子跟我借打火机点烟,完了跟我说声:「谢了兄弟。」飘然而去。问路也是。有个貌似军人的小哥,带山东腔,在某城市的地铁、高铁的地下交会处跟我问路,我指着牌子讲了一句,他大笑,走了两三步回头对我说:「哈哈哈哈这么大的字我看不到。」我跟他比个赞。他们的人情味超自然到不行,人和人没距离感(除文青和小资中产很爱谈「边界感」)。因为自然,也就不刻意。谢谢一句就好,不像台人谢谢不客气不好意思对不起个没完。东北人在陌生人之间讲话还常喊「哥」,他们的喊法好像两人本就认识或是亲戚来着。那个亲切洒脱曼妙难以形容。整个祖国你要怎么喊一个陌生路人或小贩或餐厅老板服务员,各式各样的喊法:小姐姐、大姐、大哥、叔、大叔、哥、兄弟、老同志、同志、爷爷、奶奶、姑娘、同学、小哥、老妹儿……光这个例子就很精彩生动。方言喊法暂略。
两年前我在我的网络个人空间上写,大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跟台湾中南部气息一样或相近。闽南语有句「松势」,松有轻松之意,本岛南部人、乡下人、城里的草根百姓,都有种悠然,松弛,热情,亲切,潇洒的调性,这跟整个祖国的人民群众有一样或共通的人民性。大陆人可能更悠然随便些,总之说一样也成。这个「随便」不是负面的随便。我在广州问路没一人不搭理我,有啦,有一个,我离他五公尺,我才呃请问……这兄弟立马把手里的报纸挡住脸,他正看报,干脆用上。坦白说很酷欸,我笑翻。为何我要问路?用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不行吗?我这人比较笨,有时想用传统的问路方式。
在北京地铁某站有个高大的警察,我问他通往郑州的高铁怎么走,他不开口,指着一个方向就忙别的去了,他真的太忙。他们的男男女女性子帅气「随便」到不行。这警察算是我遇到最不礼貌的,大多都礼貌得很。其实他一点也没不礼貌,只是作风干脆,随兴,豪迈。在上海南站外面我看见一个大约30几岁的大叔经过,一个跑出租车的老伯上去跟他拉客,才靠近,大叔就说:「我今天心情很差,你烦我的话我不客气了。」老伯逗他说:「心情差也要坐车啊。」大叔说:「我再警告你一次……我马上抽你……」老伯没再跟着他,事情一下子过去了,这根本不是个事儿。以上两个例子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有趣镜头,我只是随口来两段,馆长可能看不到,因为对方知道他是馆长了呀。我举的这两例子是台湾人可能看了不适应的例子,但其实你要能欣赏大陆民风的大气魄。大陆大多数人不爱计较,台湾相对容易吵架或互呛,啥都当个事儿,甚至打起来或叫警察。当然你若刷微博,他们爱计较的也不少,因为有事才拍下来,放网络上你就觉得事多。我不是说计较是错的,认真很好,要看啥状况,欠巴的人你巴下去就刚刚好。
以上两段谈都是我2023、2024在祖国看到的小镜头。
大陆同胞细腻周到,那就更谈不完了,潇洒流畅的行为中给你作点细腻的迂回表示,这种馆长有遇到,譬如一个内蒙小伙跑来上海看他,两句话就闪了,低调,不打扰,礼物留下,里面一封信。馆长读信时那个感动,靠喵,能不感动吗?大陆人一般来说很会各种表达技巧,可想而知他们把妹也是一流,馆长被把上了,没办法,只差信中称呼馆长一声:「宝,想你了。」
写到这里,你大概就可领略馆长为何爱大陆了。气息有通嘛,而且他见识到大陆在人情世故上的才华,这和做正经事、大工程、大小项目的讲究是相通的。很多台湾人喜欢讲大陆基建很棒、建筑很棒是因为政府独裁,意思是没人敢违背政策,工人多惨多惨,不敢违抗,甚至不做得劳改。事实上一个政策或项目都必须通过不断的辩论和协调才落实下去的。他们规划周延,非常会做事,且勿误解「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听过一群老蓝退伍军人聊天,他们赞扬大陆高铁的便利,最后却又集体笑说是因为独裁,而美国之所以没有啥高铁是因为民主。他们不自知荒谬无知。蓝的都这么糟了,绿的又能怎样。某种程度上,蓝营政客及其群众对大陆的偏见既深且久,难以完全矫正。而绿营的人虽然看起来极端,一旦有机会醒来,那就彻底醒了,比蓝营的人有救,且可爱聪明、智慧勇敢。
馆长回台湾有句:「大陆最美的风景不光是风景还有人。」是啊,大陆人的人味儿是他们丰硕的资产和可贵可亲的风景。当大陆某地发生天灾地变,发洪水、烧山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浩大,都可看出建国以来有种「人民性」的存续。台湾也会救灾,义消、志工也会鼎力相助,也很棒,但全城全村、联合四面八方的力量跟你拚了的那股劲头和大陆还是不大一样。就以2022年重庆的一场森林大火来说,一个平时教舞蹈的姑娘跨上一部越野机车就上路了,她也要奔赴现场,一个字,飒。几天之内群众和军警消把这个火打灭。
三,自由性,展开性(没包袱)
这么多年下来,台湾在萤幕上(包括电视、视频),讲话一点包袱也没的,我看除了李敖,当属馆长了。特色之一是都喜欢爆粗口。但这只是表征,他们思想上几乎也没任何包袱。举例来说,馆长直播的背景是上海璀璨夜景,一般政客可能得加放一张台北101大楼,不然怕被说不爱台湾。馆长不必来这套。他不怕,且没必要,他觉得他根本就很爱台湾(我补这句都多余了)。
同理,馆长谈大陆的好,谈大陆让他大开眼界,似乎也不用像书生带一句「当然我知道大陆也有大陆的社会问题和需要或提升的地方」这种废言。大多人为了表现自己客观,不得不添上这些来加强说服力。他怎么来,怎么顺,怎么样都对。他的心志状态和目标清晰,有点像打麻将手气好,全凭直觉下张子,不必太费心琢磨算牌和防守,两三下就自摸卡张(中洞)。近两个月以来他高能演出,沛然莫之能御。
李敖讲话,畅谈天下,也不做多余的「声明」和太多「铺垫」。李敖大约在二十年前曾说:「台湾人浑(亦作混;二声),香港人坏,新加坡人笨,大陆人不可测。」他爱讲啥就讲啥,不苟同的人也只好被逗笑,当然也有人抗议且挞伐。
我日前(按:七月下旬)在脸书上笑说:「搞不好以后我们看见馆长的视频背景中出现钱学森和全红婵的照片也不必意外。」同理,政客或名嘴此时也得考虑把台湾运动员或名人的照片放上去,不然怕挨骂舔共不爱台。馆长不用这套声明、澄清、避险,或讲话做太多铺垫,论述精简至极,然后送出有力的一句就对了。对绿营没啥好多说的,大家都知道绿营有够烂。
对蓝营的意识形态,馆长似乎也没啥关照一下的想法,他好像很少谈「中华民国」。这个东西他早就忘了,或自动跳过了,似乎他知道这是历史遗留,垃圾桶里的东西不谈也正常。「中华民国」旗帜亦跳过。尽管馆长没直接说自己是统派(可能是策略,他说过在岛内谈统一很危险,也可能统独问题他还没想透),但如果未来某一天他在天安门看升旗时哭了,我不意外。
也就是说,馆长走得比岛内各种颜色的政客都远,都宽,都高。起初似乎只是感性发酵,无意识的。但两个月看下来他是有意识,有自觉性的在呼应对岸谈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这九个字他用他自己一套讲话方式来发表。两岸融合,他很重视。这个融合是在精神面的融合,不是从台湾人能赚钱来出发,而是彼此融合后自然台湾人有钱赚。他的转变既是渐进的,也是提速的,一个人思想的成型本就需要时间或机遇,他的进步和升级如今可能比给他指点过的高人还高。
总结
馆长已然成为超越蓝绿白等各种颜色的人民群众代表。他是台湾中下层广大人民的一个鲜明代表人物。他的大陆粉丝有的是读书人但身上也有人民性。他自己就是一个「政党」。不是组党的意思。而是说他的粉丝或欣赏他的人在岛内或去对岸,只要讲「我是馆长粉丝」、「我是跟着阿馆的」就够了,不用特别讲自己是蓝绿白哪种或啥洨中间选民,也不必再表态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或对统一、或统一时程表有啥看法。
在政治大格局上,馆长能起啥作用,这可能无法多作期待。馆长至少正在做一件大事,就是矫正台湾人对大陆的偏见和歧视心态,且让台胞愿意用心融入大陆,彼此当一家人看,当一家人来相处。目前来看很有成效,但当然还不够。光靠他一人不行,观众和粉丝们要能相互影响,传递对的、善的、清醒的观念,要扩展出去。
馆长未来会如何,可能还是有戏,咱在此话不能说满。中国人的风潮才正开始,他不能停,人气不能散,没有回头路了。会不会最终思想又浑了,「妖风又绿陈之汉」?不知道。且看下去。基本上他有生命危险。
可想而知在台湾有统左派思想的人,或有「人民性」的人对馆长是喝采的。很容易彼此看到相同本质、属性。馆长欣喜大陆各方面建设发展的进步和人情味,统左当然也是,但以前大陆没全面发展时统左也喜欢大陆,甚至万一大陆出了闪失发展中断或下滑,统左还是喜欢大陆,亦仍盼望统一。馆长不一定像我们这样,他着重在现实生活肉眼可见的大陆万象,并思考为什么大陆能起势?人民该要的生活是什么?这一切激起他藏在灵魂中的民族情感。换言之大陆若没崛起,他对大陆可能没啥兴趣,且以后要是觉得扫兴了就可能退后一两步?但,凡民本就重视现实,对两岸大多人而言从现实出发没毛病。馆长仍正在转变和提升,他对大陆已建立很深的情感,倒也不可能三两下挫折或看到一两个不符期待的画面就容易变心。
我个人要说的是,台湾人不必高傲又自卑。台湾作为中国34个行政区里的其中一省,台湾当然有34之1的特色魅力,就像广东、陕西、内蒙、台湾都是各有各的特色精彩。就算撇开是不是个省,台湾很多东西跟大陆就是有着切不断的关系。就像三杯鸡,这是台湾民间的招牌菜,但其实来自赣南的客家庄,传到粤北或闽西客家后又辗转传来台湾。三杯的内容,是把起先的猪油改成台湾的黑麻油,江西的米酒改成台湾的米酒,酱油没啥好说。但总之江西、台湾的三杯鸡差不多,真要说台湾最不同的是放了九层塔。台湾大可不必神经兮兮啥都要捍卫或切割,否则也辜负了可爱的九层塔。
什么「小小多山的台湾」这套台湾文青用来歌咏台湾的抄袭或挪用就省省吧,就算不是抄智利国的共产党诗人聂鲁达也一样,别折腾了,九层塔拿出来洒在三杯鸡上就是真理。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有台湾的特色请安心。
2025.7.28.台北
修改于2025.8.17.
我沒那麼愛罵蔣介石,尤其當我在小紅書看到蔣友青視頻中的可愛(他精神受到很大摧殘過,目前看起來穩定),使我不忍心老罵兩蔣。蔣友青比蔣萬安可敬一百倍。
至於館長和新黨三劍客和邱毅相比,也沒比他們遜色,風格各自不同罷了。這四位頂多只有林明正比他對新中國的歷史知識懂得多,尤其林明正這幾年還花費工夫研究左翼和社會主義(館長也正大量吸收這方面,只是沒那麼學術,他光研究大陸如何扶貧就值得點讚)。還有,林明正的論述能力一直在進步中,我聽過他講演,很能講,甚至比視頻中還棒。我不認識林明正,只是我的觀察如上。
淺一點來說,林明正在微博曾說自己看過大決戰三部曲的電影,館長可能才正要補課。蘇恆、王炳忠、邱毅可能也看過,但可能沒法像林這麼會聊或愛聊這種話題。要懂大陸要花時間,而且不能有成見。譬如大陸網友講林總、林帥、101,指的是林彪。鄧小平代號叫總設計師。毛主席叫教員。館長不必懂這麼細,不然他一天可能只睡一小時。館長最近看到1984年大陸閱兵的畫面而驚嘆,這我早已預料有大陸網友會告訴他,因他很愛看網友留言。不是每個網紅或大V都很愛自己的粉絲,頂多留言看兩眼,架子大,懶得回也罷,更不肯學習。
兩岸閱兵史,我三年前寫過一篇可參考:
https://wczhang.blogspot.com/2022/08/blog-post_28.html
館長目前不足的是無法看到大陸中下層老百姓怎麼生活,他只看大陸尖端發展的一面。如果他能看到前者,他會更讚賞大陸。
我將上個月寫的館長一文重新整理,刪掉幾千字,又新增幾句,總共留下8000字,還是很多字但不得不。在此用簡中貼出。繁體連結則在此:
https://wczhang.blogspot.com/2025/08/blog-post_18.html
以下容我佔用版面多一點,因我要貼簡中之全文。目的是方便大陸網友轉貼,這樣才更理解館長這個人。我私下不認識他,包括本篇前面提到的人名我沒一個私下認識。但我認為我看得出他的成色。電影天下無賊有過一句很好笑,黎叔(葛優)說:「我倒是有興趣,驗驗這對鴛鴦的成色。」指的是劉德華、劉若英。反正很好笑就對了。我不是說我是武林至尊黎叔的意思,只是借用「成色」。
《开弓没有回头箭:馆长陈之汉首次大陆行的转变》
一,馆长的进步性
2025年馆长六月上旬到中旬首次前往大陆,近两个月来堪称震撼台湾,且六次登上央视(截至8月17日为止;本文原稿写于7月28日,此为浓缩版)。
很多台湾人讶异他怎么变得这么会讲。
惊艳的不光是馆长思想转向,而是他很会讲,口才极佳。很多人觉得他以前很废,倒不是他挺过谁,一码归一码,他脑袋和口条很贫乏,所谓论述能力,很菜。又如他的搞笑,对打,譬如跟啥“吃屎哥”,低能到不行。两岸许多网友喜欢他爆粗口,当他是乐子人,或崇拜,大多都是压抑惯了,或生活太过乏味?
馆长是如何顿悟的?他的智慧是如何升级的?这带来一个启示,人人都可以是食神。
简单说,人一旦开窍了,一通百通。粤语叫:「一理通百理明。」
我的观察和研判,他的开窍跟他私下研究大陆,看各种视频,往返两岸的本岛民间人士跟他聊大陆有关。以及可能有高人指点。
很多台湾同胞至今不晓得,大陆视频、文章、影视的素质很高(大陆观众认为很多影视低能或乱拍另当别论),所谓高手在民间,各路专业的人都很多,各种面向十分之灿烂。馆长从中吸收到养分,加上有慧根,整个开窍。
2024年大陆B站的女性博主“吃瓜蒙主”曾说,台湾教育失败,台湾人讲话和写东西不利索,没法清清爽爽,文章无法理得明明白白,台湾人的文化越来越次。顺着蒙主这番话来说,馆长默默吸收了许多大陆视频的灵气,如今脑子和口条理得明明白白,智慧豁然升级。
他在前往大陆前就开窍一半了,去大陆只是印证看法,印证过后自而信心百倍,全然开窍。此人是做生意的,竟然还46岁了没去过大陆。他很想去!想去就学得更多。大陆能学到的、能见识的东西太多了。
一字记之曰:心。
从接触大陆资讯到前往祖国,起初是好奇,尤其是想给绿营难堪,基于恨绿,但这演变成他发现自己被台湾蒙蔽了,所谓台蛙,信息茧房,他发现这事儿得认。认自己过去脑残。
从而他为过去道歉多次,试问蓝绿白政客网红有无对自己歉疚半次过。不是说他道歉多伟大(他也是不得不),但已然不容易了。
他一通百通之后,慨然讲出祖国、中国人、大陆,以及用他简单精准的俗白方式来论述两岸走在一起的重要。包括他想止战,想拉下绿营,想救柯文哲。这些都很打动人呀。
事实上当他首次造访大陆,来到上海落地的第一天,做直播时仍不断中国、中国的讲话。第二天就改成大陆。后来他告诉大家,大陆群众有人告诉他为何要讲大陆,我们对台湾同胞这么友善,听你们老讲中国伤感情。意思就是你们有分别心。可以看出「伤感情」这句让馆长很在意,颇内疚。大陆同胞的真诚,让馆长也变成一个真诚的人,那些表情是演不来的。
这不光是人情世故的假来假去,而是在意伤感情,这种人特别成熟智慧,心肠也好。他伤了别人感情,别人有点受伤,他也跟着受伤,他有这种体会能力,这种人不容易。本人2009年曾前往台大聆听侯孝贤导演一场文艺讲演,他建议台下青年:「要能感受别人的感受。」眼下是十六年后的2025年,读书人普遍有无作到这句值得打个问号,可状似大老粗的馆长却体现了这句。
他的思想和口条表达能力是一起进步的,这种进步才叫扎实,也生出了魂魄。从个人的进步,到民族情感、两岸情感的对接,一瞬间他彻底接通了一切。有点素人禅师的味儿了这是。
二,馆长的人民性
本单元较长,分三小单元。三小并非闽南语粗口,亦可能我来个擦边胡闹。
1、志愿役的傻逼
事实上,有不少台商、台生(尤其去大陆的短期交换生)即使常在、或曾在大陆生活,但对大陆多少带着歧视眼光。他们非常需要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遇到彼此有利益关系或精台的大陆同胞更是烂在一块儿。
可喜的是馆长不是这种人。这跟馆长的阶级背景可能有关。他是祖籍宜兰的台北人,但属底层草根气息。他当兵签下陆战队志愿役。从资料来看是「转服」,即入伍新训后从义务役改签转服志愿役。基本上签下转服志愿役的多半是草根、中产家庭或一般保守家庭长大的。
坦白说这种人在军中常被人背后取笑。只因被认为是没出息的笨蛋,当兵这种鬼日子,国军那么腐败,却签下去。他们一门心思在军中老实存钱,但被很多弟兄私下讥笑是浪费青春,没有进取心,不敢在社会上闯荡。有些志愿役在部队当个士官就骄横,还爱讲当士官背责任多苦。不少底层弟兄在国民中学因不爱念书,辍学后学习了一门手艺就收入不少;譬如学木匠、修水电、做铝门窗等,老年代的收入更多。他们看不上签志愿役的废物(喂),大专兵本身的优越感就不用说了(大专兵烂透在军中是共识),他们也看不上志愿役。
一般来说,在台湾当兵不像大陆人加入解放军的光荣感那么大,取笑转服的人是常态,甚至退伍后在社会上仍被人笑问:「奇怪你当初怎会签下去?」、「军中成天在造假你受得了?」、「你这么爱当兵不如早几年进士校或考官校?」问题是官校入学的成绩不能太差。有的大专兵在新训中心(竟然)自愿转服预官,这也是签下志愿役的一种,背地里遭笑话亦属常态。
在此还得说明一下,以前的志愿役士官是有区分的。如果你是国中毕业去读士校的那种志愿役,在军中好受人尊敬,他们清一色出身寒门,被爸妈叫来读士校,特能吃苦,身上有战技,下部队后本职学能很强,一路当到上士退伍。可如果你是20岁或19岁入伍(一般20岁收到征兵令,馆长自愿申请提早一年当兵),之后在新兵训练中心被军方游说后改签的转服,这种容易被弟兄们看不上,菜的时候还被老兵欺负算正常。这种大概当三年半、23-24岁中士退役,除非你再签下去。本岛部队长年是老鸟爱欺负或霸凌菜鸟,甚至虐出人命,老鸟常说这叫「传统」,或流行骂兵:「你这个死老百姓。」这不是大陆以人民军队做号召的文化能想象的。
谈这些绝不表示看不起人是对的,只是讲解老年代志愿役在军中的生态文化。每个人的生涯规划都必须被尊重,每个人家庭状况不同。
话回馆长,他曾在网络上谈自己在陆战队吃了苦,受了折磨,被整冤枉,似乎没吃到太多志愿役的红利。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台湾很多男人退伍后喜欢谈当兵吃苦、多操、多惨烈,虽难免有欢乐吹牛成份(女人根本懒得听),但如果当事人把吃苦的价值、荣誉放得很高,这种人通常没有辜负他受的罪,是个真男人,他们之后回到社会上都韧性十足。
馆长1979年生,照理说他服役时本岛部队训练变成很轻松了,但海陆属特种兵,仍有一定程度的艰辛「遗绪」传下,多少仍具谈资,他重视军中吃的苦,这值得给他点赞。他就算没当网红,单单能从谷底、憋屈的各种阶段一路摸爬滚打而至奋起创业,完成了开设健身房的人生梦想,在社会上寻得一席之地,这已然值得尊敬。当然这不是说他事业无成的话就该被看低,我自己就一事而成可不是。
在馆长的年幼时期,本来家境挺好,然因父亲早逝,家里有点家道中落,才让他变成类似草根阶级。一般来说,什么阶级就带来什么气息,但有时也不准确,有的人接地气的天赋高、慧根够,自可融合巧妙。李敖是读书人但有少见的草莽性格,有流氓气。馆长不是读书人但讲话比读书人精准有料。民间很多平民百姓或读书人都很爱聊政治,但像馆长能聊出含金量的,坦白说不多。他比「话糙理不糙」的大妈大爷还厉害,而且他其实内容并不糙。甚至他的大块头模样、年轻时的道上色彩、浓郁的草根气息,反而都成了障眼法。就像古早时期唱铜锤花脸的金少山,扮相和声腔是一个粗勇豪迈、大嗓门的人,但心思细腻得很,绝对称得上是艺术家。
举凡(以前我服役时的连长成天爱讲举凡)阶级背景、草根气息、工农兵的味儿、志愿役经历之种种,看来对馆长这人的基调有很大的影响。简单说,这种摸爬滚打、吃过苦的孩纸对人比较能用平常心,平等心去相待,去搏感情。而且馆长可贵的是模样憨厚(或憨傻),这种人重视真心,相信真心,并不会变油。
说到憨厚,固然台商也有很多是草根大老粗、农工兵子弟出身,可前面讲到不少台商对大陆心态不好(我相信台商们都开心馆长来大陆,但这和台商在大陆爱吹牛且多少带点高姿态的德行是两回事),中产小资出身的台商当然大多也蛮糟,但馆长这人并非如此。馆长对大陆的可说动了真情,憨憨的,这是他的独特性,这点蛮珍贵。倒也不能全用阶级来套,譬如有些人家世不错但对大陆的心态很友善,当然这种人在岛内也对各种人不会有成见,不会自以为高尚,总之这种人是极少数。说到底台湾人不分阶级背景学历贫富南部北部,大多就是看不上大陆,很爱用台湾人的身份来靠夭,来讲大陆这个那个的。这种鸟样子是蓝绿统治本岛几十年来造成的。其中文青的嘴脸尤其糟糕。大陆文青也烂,也看不上大陆,自认洋派的作家、导演、公知和文青一大把。还好馆长没接触这种二百五。馆长接触的大陆属「人民群众」居多,气味相投或相近。算他运气好。
2、志仁补校的无敌学历
馆长的履历中最牛的不是志愿役的憋屈,而是,靠杯,他来自台北最接地气的几所「烂」学校之一。他读过协和工商,最后在志仁补校毕业。协和当然很废,志仁更废,说废到最底部不算污辱。开玩笑的,此「废」有生命力之意。协和的女生在我那个年代很正,她们比较不爱念书,只是这样。我记得以前协和的男生少。高中时,我们班上有些被留级的同学,他们跟我挺要好的,他们升不上高三,留级高二,然后撑一年后好几个要转去志仁洗学历,这些好友被爸爸骂干、或揍翻,少不了被骂败家子。可见我这几个同学有多杰出!他们很聪明但就是不想念书,坐不住,爱玩。这些被俗世看不上的学历(根本拿不出手的学历)反而是他们生命力昂扬又靡废的人生资产。
摊开馆长的成长史,他的年纪恰恰接到这些学校充满特色的年代。全省以前还有许多五专、三专、二专,都很接地气。同理,多少也有刻板印象,我表妹(1976年次)是中国工商(五专时期)毕业的,她一直很乖巧且聪慧。
我曾执教过一年高职夜间补校。当时是90年代中期在基隆。补校都是在晚上上课,学生大多白天打工。这批孩子有一半年龄和馆长相仿,他们不爱念书(学习)或因缘际会失去学习机会,白天学手艺或做粗工,晚上来补校是花钱洗学历,希望自己拥有一张高中或高职文凭。男同学大多江湖气重,有的年纪还比我这个老师大。女生倒是不惹事,只是接地气。
我那年当高三补校的班导(班主任),一次同学们上课聊天的声音太吵,我走到一个坐最后一排的男生面前,把他身边没人坐的一把空椅子高高举起,在他面前砸烂,木头椅子粉碎一地。全班鸦雀无声。这男生羞愤,他个儿高,整个人跳起来,飙粗口,叫板「出来讲!」闽南语,意思邀我去走廊打一架。这人平时本就流氓味,一时间对峙起来……
我心想这下完了,缓和自己情绪十来秒钟后,我不卑不亢的跟他诚恳说:「是我冲动了,我跟你道歉。」从而危机化解。此后班上许多男孩子对我更热情,当我是铁哥们。他们几度激动的对我说:「我们长这么大没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过对不起。」其实我一半的原因是怕挨揍,另一半原因是多年来从小本就有错会主动认错,且认了反而轻松,我对真理的兴趣大过面子。这个对我暴粗口的男生后来对我相当义气帮忙。略下。
他们是被社会看不上或歧视的孩子,有人对他们好,他们跟你拿心换心。
所以为何我看得懂馆长觉得他很可以,这是基本的人生阅历。(这两句啰唆了,根本不必我这些生活经验观察接触,我想你也看得懂的。)
3、新中国的活泼松势和细致多情
众所周知,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是以无产阶级立国的,至今(2025)七十六年来虽然历经思想路线斗争动荡和选择,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改成自由经济,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还是在,人民性的气息还是化在每一代人的风格中(大陆文青例外啦干),他们大多作风一派自然流利,潇洒得很,很接地气,不矫情,不装逼。
譬如我在大陆,一个男子跟我借打火机点烟,完了跟我说声:「谢了兄弟。」飘然而去。问路也是。有个貌似军人的小哥,带山东腔,在某城市的地铁、高铁的地下交会处跟我问路,我指着牌子讲了一句,他大笑,走了两三步回头对我说:「哈哈哈哈这么大的字我看不到。」我跟他比个赞。他们的人情味超自然到不行,人和人没距离感(除文青和小资中产很爱谈「边界感」)。因为自然,也就不刻意。谢谢一句就好,不像台人谢谢不客气不好意思对不起个没完。东北人在陌生人之间讲话还常喊「哥」,他们的喊法好像两人本就认识或是亲戚来着。那个亲切洒脱曼妙难以形容。整个祖国你要怎么喊一个陌生路人或小贩或餐厅老板服务员,各式各样的喊法:小姐姐、大姐、大哥、叔、大叔、哥、兄弟、老同志、同志、爷爷、奶奶、姑娘、同学、小哥、老妹儿……光这个例子就很精彩生动。方言喊法暂略。
两年前我在我的网络个人空间上写,大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跟台湾中南部气息一样或相近。闽南语有句「松势」,松有轻松之意,本岛南部人、乡下人、城里的草根百姓,都有种悠然,松弛,热情,亲切,潇洒的调性,这跟整个祖国的人民群众有一样或共通的人民性。大陆人可能更悠然随便些,总之说一样也成。这个「随便」不是负面的随便。我在广州问路没一人不搭理我,有啦,有一个,我离他五公尺,我才呃请问……这兄弟立马把手里的报纸挡住脸,他正看报,干脆用上。坦白说很酷欸,我笑翻。为何我要问路?用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不行吗?我这人比较笨,有时想用传统的问路方式。
在北京地铁某站有个高大的警察,我问他通往郑州的高铁怎么走,他不开口,指着一个方向就忙别的去了,他真的太忙。他们的男男女女性子帅气「随便」到不行。这警察算是我遇到最不礼貌的,大多都礼貌得很。其实他一点也没不礼貌,只是作风干脆,随兴,豪迈。在上海南站外面我看见一个大约30几岁的大叔经过,一个跑出租车的老伯上去跟他拉客,才靠近,大叔就说:「我今天心情很差,你烦我的话我不客气了。」老伯逗他说:「心情差也要坐车啊。」大叔说:「我再警告你一次……我马上抽你……」老伯没再跟着他,事情一下子过去了,这根本不是个事儿。以上两个例子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有趣镜头,我只是随口来两段,馆长可能看不到,因为对方知道他是馆长了呀。我举的这两例子是台湾人可能看了不适应的例子,但其实你要能欣赏大陆民风的大气魄。大陆大多数人不爱计较,台湾相对容易吵架或互呛,啥都当个事儿,甚至打起来或叫警察。当然你若刷微博,他们爱计较的也不少,因为有事才拍下来,放网络上你就觉得事多。我不是说计较是错的,认真很好,要看啥状况,欠巴的人你巴下去就刚刚好。
以上两段谈都是我2023、2024在祖国看到的小镜头。
大陆同胞细腻周到,那就更谈不完了,潇洒流畅的行为中给你作点细腻的迂回表示,这种馆长有遇到,譬如一个内蒙小伙跑来上海看他,两句话就闪了,低调,不打扰,礼物留下,里面一封信。馆长读信时那个感动,靠喵,能不感动吗?大陆人一般来说很会各种表达技巧,可想而知他们把妹也是一流,馆长被把上了,没办法,只差信中称呼馆长一声:「宝,想你了。」
写到这里,你大概就可领略馆长为何爱大陆了。气息有通嘛,而且他见识到大陆在人情世故上的才华,这和做正经事、大工程、大小项目的讲究是相通的。很多台湾人喜欢讲大陆基建很棒、建筑很棒是因为政府独裁,意思是没人敢违背政策,工人多惨多惨,不敢违抗,甚至不做得劳改。事实上一个政策或项目都必须通过不断的辩论和协调才落实下去的。他们规划周延,非常会做事,且勿误解「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听过一群老蓝退伍军人聊天,他们赞扬大陆高铁的便利,最后却又集体笑说是因为独裁,而美国之所以没有啥高铁是因为民主。他们不自知荒谬无知。蓝的都这么糟了,绿的又能怎样。某种程度上,蓝营政客及其群众对大陆的偏见既深且久,难以完全矫正。而绿营的人虽然看起来极端,一旦有机会醒来,那就彻底醒了,比蓝营的人有救,且可爱聪明、智慧勇敢。
馆长回台湾有句:「大陆最美的风景不光是风景还有人。」是啊,大陆人的人味儿是他们丰硕的资产和可贵可亲的风景。当大陆某地发生天灾地变,发洪水、烧山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浩大,都可看出建国以来有种「人民性」的存续。台湾也会救灾,义消、志工也会鼎力相助,也很棒,但全城全村、联合四面八方的力量跟你拚了的那股劲头和大陆还是不大一样。就以2022年重庆的一场森林大火来说,一个平时教舞蹈的姑娘跨上一部越野机车就上路了,她也要奔赴现场,一个字,飒。几天之内群众和军警消把这个火打灭。
三,自由性,展开性(没包袱)
这么多年下来,台湾在萤幕上(包括电视、视频),讲话一点包袱也没的,我看除了李敖,当属馆长了。特色之一是都喜欢爆粗口。但这只是表征,他们思想上几乎也没任何包袱。举例来说,馆长直播的背景是上海璀璨夜景,一般政客可能得加放一张台北101大楼,不然怕被说不爱台湾。馆长不必来这套。他不怕,且没必要,他觉得他根本就很爱台湾(我补这句都多余了)。
同理,馆长谈大陆的好,谈大陆让他大开眼界,似乎也不用像书生带一句「当然我知道大陆也有大陆的社会问题和需要或提升的地方」这种废言。大多人为了表现自己客观,不得不添上这些来加强说服力。他怎么来,怎么顺,怎么样都对。他的心志状态和目标清晰,有点像打麻将手气好,全凭直觉下张子,不必太费心琢磨算牌和防守,两三下就自摸卡张(中洞)。近两个月以来他高能演出,沛然莫之能御。
李敖讲话,畅谈天下,也不做多余的「声明」和太多「铺垫」。李敖大约在二十年前曾说:「台湾人浑(亦作混;二声),香港人坏,新加坡人笨,大陆人不可测。」他爱讲啥就讲啥,不苟同的人也只好被逗笑,当然也有人抗议且挞伐。
我日前(按:七月下旬)在脸书上笑说:「搞不好以后我们看见馆长的视频背景中出现钱学森和全红婵的照片也不必意外。」同理,政客或名嘴此时也得考虑把台湾运动员或名人的照片放上去,不然怕挨骂舔共不爱台。馆长不用这套声明、澄清、避险,或讲话做太多铺垫,论述精简至极,然后送出有力的一句就对了。对绿营没啥好多说的,大家都知道绿营有够烂。
对蓝营的意识形态,馆长似乎也没啥关照一下的想法,他好像很少谈「中华民国」。这个东西他早就忘了,或自动跳过了,似乎他知道这是历史遗留,垃圾桶里的东西不谈也正常。「中华民国」旗帜亦跳过。尽管馆长没直接说自己是统派(可能是策略,他说过在岛内谈统一很危险,也可能统独问题他还没想透),但如果未来某一天他在天安门看升旗时哭了,我不意外。
也就是说,馆长走得比岛内各种颜色的政客都远,都宽,都高。起初似乎只是感性发酵,无意识的。但两个月看下来他是有意识,有自觉性的在呼应对岸谈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这九个字他用他自己一套讲话方式来发表。两岸融合,他很重视。这个融合是在精神面的融合,不是从台湾人能赚钱来出发,而是彼此融合后自然台湾人有钱赚。他的转变既是渐进的,也是提速的,一个人思想的成型本就需要时间或机遇,他的进步和升级如今可能比给他指点过的高人还高。
总结
馆长已然成为超越蓝绿白等各种颜色的人民群众代表。他是台湾中下层广大人民的一个鲜明代表人物。他的大陆粉丝有的是读书人但身上也有人民性。他自己就是一个「政党」。不是组党的意思。而是说他的粉丝或欣赏他的人在岛内或去对岸,只要讲「我是馆长粉丝」、「我是跟着阿馆的」就够了,不用特别讲自己是蓝绿白哪种或啥洨中间选民,也不必再表态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或对统一、或统一时程表有啥看法。
在政治大格局上,馆长能起啥作用,这可能无法多作期待。馆长至少正在做一件大事,就是矫正台湾人对大陆的偏见和歧视心态,且让台胞愿意用心融入大陆,彼此当一家人看,当一家人来相处。目前来看很有成效,但当然还不够。光靠他一人不行,观众和粉丝们要能相互影响,传递对的、善的、清醒的观念,要扩展出去。
馆长未来会如何,可能还是有戏,咱在此话不能说满。中国人的风潮才正开始,他不能停,人气不能散,没有回头路了。会不会最终思想又浑了,「妖风又绿陈之汉」?不知道。且看下去。基本上他有生命危险。
可想而知在台湾有统左派思想的人,或有「人民性」的人对馆长是喝采的。很容易彼此看到相同本质、属性。馆长欣喜大陆各方面建设发展的进步和人情味,统左当然也是,但以前大陆没全面发展时统左也喜欢大陆,甚至万一大陆出了闪失发展中断或下滑,统左还是喜欢大陆,亦仍盼望统一。馆长不一定像我们这样,他着重在现实生活肉眼可见的大陆万象,并思考为什么大陆能起势?人民该要的生活是什么?这一切激起他藏在灵魂中的民族情感。换言之大陆若没崛起,他对大陆可能没啥兴趣,且以后要是觉得扫兴了就可能退后一两步?但,凡民本就重视现实,对两岸大多人而言从现实出发没毛病。馆长仍正在转变和提升,他对大陆已建立很深的情感,倒也不可能三两下挫折或看到一两个不符期待的画面就容易变心。
我个人要说的是,台湾人不必高傲又自卑。台湾作为中国34个行政区里的其中一省,台湾当然有34之1的特色魅力,就像广东、陕西、内蒙、台湾都是各有各的特色精彩。就算撇开是不是个省,台湾很多东西跟大陆就是有着切不断的关系。就像三杯鸡,这是台湾民间的招牌菜,但其实来自赣南的客家庄,传到粤北或闽西客家后又辗转传来台湾。三杯的内容,是把起先的猪油改成台湾的黑麻油,江西的米酒改成台湾的米酒,酱油没啥好说。但总之江西、台湾的三杯鸡差不多,真要说台湾最不同的是放了九层塔。台湾大可不必神经兮兮啥都要捍卫或切割,否则也辜负了可爱的九层塔。
什么「小小多山的台湾」这套台湾文青用来歌咏台湾的抄袭或挪用就省省吧,就算不是抄智利国的共产党诗人聂鲁达也一样,别折腾了,九层塔拿出来洒在三杯鸡上就是真理。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有台湾的特色请安心。
2025.7.28.台北
修改于2025.8.17.
兩岸議和團 © 2022 - 2026